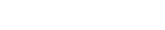深秋的田野,只有高粱还挺着高傲的头颅。金色的稻田,一茬茬地收割,都已颗粒归仓。留下几粒稻穗,一群鸡在寻啜着。
高瑞珍一个人呆在棉花田里。7亩棉田,采完东边的,西边那丘又吐出了。丰收有喜悦,但她也有“哀怨”:“都是他闹的。我本来在工厂里打零工挺好的,每个月上十来天班,有2000元收入。非得要自己承包田来种棉花,我也只能呆在田里了。”
她的“他”,是兰溪市水亭畲族乡农技站长项庆奶,51岁,戴副眼镜,身穿黑点衬衫,脸庞黝黑。看着妻子双手打着的五六个创可贴,他腼腆地笑笑:“我们老家的田几年前就被征用了,我包了这块田,又让她风吹日晒了。”
1985年,原汪高岭乡招农技员。项庆奶专业对口,一举考中。2000年,他调入水亭,2006年成了水亭乡农技站站长。
长年与农业、农民打交道,养成他纯朴又直率的性格。而农业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显得弱势,又让他很担忧。
“兰溪本来是没有抛荒田的,这些年也能看到了。种田的也都是些老农民,勤劳、保守,不愿尝试新种植方法。”项庆奶说,这就是他承包田的原因。水亭乡有5000亩棉花田,棉花田里套种鲜食春大豆效益不错,但没人愿意尝试。这项技术在水亭推广不开。
说给农民听,不如种给农民看。去年,项庆奶包了1.2亩地小搞搞,收益不错。棉花收入不算,光鲜豆荚就卖了1000元。今年,他加大力度,一口气把边上的几亩抛荒田全包了。
3月种春大豆,5月播棉花;6月收大豆,10月起摘棉花。项庆奶白天上班,根本忙不过来。已转行为产业工人多年的妻子,又被叫回到田里。“还是工厂好,有姐妹们说说话,不要风吹太阳晒的,手也不会被棉花梗戳得七孔八洞的。”高瑞珍说。
项庆奶憨憨地笑着说:“不要着急,已经有农民‘上钩’的了。隔壁田的周阿喜几次问我要春大豆的种子;还托我买棉花脱叶催熟剂。”
农业种植,坐在办公室想想,与自己亲身体验是截然不同的。项庆奶把妻子“拖下水”,就得受妻子抱怨。比如,早晨采棉,露水太湿,棉花叶太多,采摘不便。“我就在想,人家新疆是怎么办的?我上网仔细看新疆的新闻,发现他们棉花采摘时,几乎没什么叶子。”项庆奶发现这个秘密后,迅速找到了新疆农垦科学院,请求技术支持。原来,他们用了一种棉花脱叶催熟剂。在70%棉桃裂开时用上,7天后叶子就能脱掉,20天后能够快速吐絮。
看着叶子脱掉,看着棉桃吐絮快,周阿喜到项庆奶的试验棉田,比到自家的田还勤。“我也要学点来。每年采棉花时,都被家里人抱怨难采呢。”周阿喜告诉记者。
在棉花田里,项庆奶算了笔账,今年棉花品种有“中棉所87”和“鄂棉10”,亩产260公斤,按照目前每公斤6.4元的收购价,7亩地的效益达11648元。6月收获的春大豆亩产250公斤,收购价每公斤5元,效益8750元。一年种下来,收入突破两万元。
“那是普通农民家会有的收入。我们的田是每亩600元一年包来的,采棉花、采豆荚我忙不过来,全是雇人的。雇工费一除,也没几个钱了。”高瑞珍又“戳穿”了老伴。但她也说,老项是想给农民试验一条科技增收的路子,她虽有抱怨,心底里也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