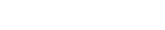临近教师节,各路均有问候。老师之间,也自娱自乐,常互致排比句。有问候也是好的,我只怕采访,特别怕遇上语文不好的记者,一定要让你说场面上的话,幸福啊,快乐啊,光荣啊……如果你坚决不说,他会给你添上几句。
没有必要把教师职业神圣化,把教师尊崇到不食人间烟火,大家都不方便。人们不爱思考,让一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话,流传多少年,仔细想想,在“人类灵魂”上做手脚,你不觉得恐怖吗?
教师是个古老而普通的职业,和石匠铁匠厨师农夫,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你认为我这句话不够意思的话,可以像我一样当教师,然后一直做到退休,那时就会明白我没乱说。当教师的,即使被别人顶着捧着,也不能头晕,以为高人一等;教师如果能平等地看待每一种职业,他就会明白自己的“职责”,他就能“教”了。
不一定要有教师节,如果社会经常反思教育,让教师在平静的环境中工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比过教师节好。但我并不认为现在就要动手取消教师节。商业社会,事多节多噱头多,教师节没沾坏习气,则不妨过过。“龙虾节”“螃蟹节”,是官场招商引资,聚会朋友,如“油条节”“包子节”,就不必了。“护士节”关注一下护士,“教师节”关注一下教师,当年设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比起文革肆虐,能这样礼貌地意思一下,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中国,一定要保留几个清苦而崇高的职业,令人们向往留骨而贵,而鄙薄曳尾涂中之徒。最早的几次教师节庆祝会,仪式隆重,各级官员慰问,小朋友朗诵赞美诗,宣读表彰名单,礼成,各人回班上课,回办公室改作业。然而,后来的教师节,就比较重视物质了。
为慰问老师,教师节大会上,从教达到一定年限的教师会获得纪念品,先后有腈纶被、羽绒被、太空棉被或毛毯,按年限,所给不等;一排教师上台站好,校方把硕大的被子一件一件地朝台上搬,领导行握手礼,向老同志授被,让他们抱着被子与领导合影。但见照片上一团一团的被子,被子上露出个脑袋,像央视上的“视察灾区”。倒是学生见怪不怪,逢年过节,看老师拎着扛着学校发的桶装油、水果箱、大米、肉食回家,会很知己地告诉老师:“我们小学过节还发过盐水鸭、猪脚爪呢!”
有一年轮我接受慰问,校领导很知己地打招呼:放心,保证不让大家在台上捧被子。我立刻大感欣慰,表扬他们从善如流。后来有通知:都放在工会办公室了,会后领回家。拎着床被子,行走在校园里,接受学生的致意,尴尬多于自豪。
世人好出大言,旧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话让有脑袋的人吃不消,让成千上万的人认你为“父”,你就成笑料。“一日为师,终生为友”?也不可能,谁能记住那么多人的高姓大名?学生年纪小,不要教他们这些陈腐之言,要培养一点儿现代意识。七八年前,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师生之间不存在什么“恩”》,我的意思不复杂:要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社会对教师职业和师生关系要有正确认识;社会认为老师“有恩”于学生,无非是认为过多地付出,做了世上多数人不愿做、无力做的事;国民教育由国家投入,以启蒙昧,利在民族,教师受雇于国家,服务社会,谈不上“施恩”于人,何至于要让人“报恩”?文章发表后招致严厉批评,有人认为我竟至于糊涂到不知“师恩难忘”,有文章则宽容地放我一码,说“考虑到作者是老教师”,否则将不知会“报”我一点什么了。编辑很开心,说,好啊,争起来了,这下热闹了,你再写、再写!可我感到累,本来就忙得事情做不清,还要和强行报恩的人缠在一块争辩教育常识,更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