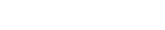当新版《雷雨》遭遇笑场的时候,我丝毫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因为我也是笑场的一名观众,只不过不是在公益场,但是当杨立新开始发微博批评笑场的时候,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件大事了。
我并不想再过多地叙述观众在何时何情节下笑场以及笑场的原因了,因为之前太多的评论者和观众对此进行了论述,在本文里,我更关注的是艺术工作者应该如何面对“被笑场” ,应该如何去面对观众的批评,艺术、艺术工作者和受众之间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观众笑的是《雷雨》还是新版《雷雨》 ?
即便是公益场的学生观众,他们也未必没看过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 ;即便学生观众们之前丝毫不知道《雷雨》 ,其他非公益场的观众,特别是那些熟悉中国文学的戏剧资深观众,不可能不知道《雷雨》 ,这些观众为何也会发笑呢?
作为一名笑场者,在我高中学习《雷雨》这篇课文的时候,在我成年后看全部剧本的时候,在我脑海中开始浮现周朴园、鲁侍萍、周萍等形象的时候,我丝毫没有笑过,反而会给我深刻的思考。但是当我看了新版《雷雨》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发笑?
显然,我笑的不是曹禺先生的《雷雨》 ,而是杨立新等众位艺术家们所演出的《雷雨》 ,这两个《雷雨》是不能画等号的。
我,作为一个30多岁的观众,当听到四凤那刺耳的叫声、看到四凤那几乎要撕扯衣服的动作时,我实在忍不住嘲笑了。
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纯洁善良的四凤会有如此夸张、不知所措的表演:这既不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式的表演——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在鲁侍萍那样的管教下,四凤可能是那样外化甚至“奔放”的吗?她可能会那样歇斯底里地高声尖叫,做出双臂大开大合,甚至要扯开自己的衣裳的动作吗?它也不属于布莱希特所主张的那种“间离”似的表演:四凤的那种动作毫无节制和美感,演员的确告诉了观众她是在表演,但是它产生的不是“间离效果” ,而是“隔离效果” 。
同样,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周萍会成了一个吊儿郎当、腻腻歪歪的青年男人。因为在曹禺的笔下,周萍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纨绔子弟,他原本有思想,有文化,有冲破束缚的渴望,所以才敢和后母偷情;但是他缺乏反抗父亲的勇气,他无法彻底背叛这个家庭,他是一个“矛盾体” ,他一切内心的挣扎最终表现为外在的“玩世不恭” 。这绝对不是现在王斑所呈现的那种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的傀儡儿子形象。
戏剧,是二次创作艺术,剧本和现场演出所给予观众的,必然是相近但并不相同的意象。很简单的道理,当我看剧本时,我是直接感悟,当我看演出时,我是间接感悟;所以观众笑场,根本上说是因为舞台呈现与剧本呈现相差太大。
2、笑场是不尊重艺术、不尊重演员吗?
斯琴高娃就此事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提到观众应该“尊重艺术” 。笑场,真的是不尊重艺术吗?
艺术,无论对于创作者来说,还是对于接受者来说,其“酒神”精神的一面决定了它需要人们的直接反应,这既包括了当人们喜爱的时候“歌之舞之” ,也包括在不喜爱的时候,直接的笑之拒之。艺术本身所追求的“真善美” ,不仅仅是体现在艺术作品上,也包括在创作过程和接受过程上。我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假模假式地点头鼓掌微笑……假!
其实,观众的笑是会心的,直接的,不是故意的,更不是起哄似的,我可以直言:作为在现场直接感受到笑场的观众,上述的表述是不含任何水分的。这些基于艺术作品的直接反应。
那么观众的笑场是否又是不尊重演员呢?我想这恰恰是对演员真尊重,因为你付出了,我就要对你的付出负责——因为在理论上,一个对艺术负责的演员,他需要通过观众的反馈来知道自己的实践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尊重的基础,是真诚,不是隐瞒。
观众鲜有机会直接找到主创人员去表达他们的观点;观众又不能直接在台下喊倒好,高声叫骂;他们只有用“笑”这样最直接反应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观点。
3、艺术家们为什么不能接受观众笑场?
顾威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观众不该笑的地方笑了,不合情理,但他对观众笑场表示要正确对待,他对观众笑场的感受没有主演杨立新那么强烈。
观众是故意捣乱吗?所谓的艺术家们真的了解观众吗?
我相信主创们对工作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但请不要奢望让观众把对这种态度的理解转变为对最终艺术作品的容忍,观众的苛刻是对艺术工作者最好的支持——任何一位艺术家都知道这句话:不要让家长溺爱孩子。
如果这些人能够像马连良、谭富英那样遭遇过被叫“倒好”的考验,如果这些人能够像梅兰芳那样反思鲁迅的批评,他们会用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这个事件。
(转自中国艺术报/满羿)
票务代理:永乐票务
订票电话:4006-228-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