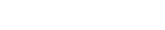难倒耍猴人的“运输证”
10月21日,距“霜降”两天,鲍凤山、鲍庆山兄弟俩还在河南新野县鲍湾村的家中。往年此时,他们已在秋收后出去耍猴。外出耍猴卖艺二三十年,受的委屈不可胜数,可鲍凤山说“都没这次惨”。
7月10日,鲍凤山等人牵着猴子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街头演出。此前他们从南阳坐车到沈阳,发现当地有个国际会议,就有“自知之明”地搭上了去牡丹江市的列车。
当日中午,鲍凤山和同伴正在牡丹江市文化广场步行街表演猴戏,两名森林公安要“带走”他们,并开始往车上推。后来他们被刑拘,因为猕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他们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
他们两次共被刑拘了54天。 9月23日,牡丹江市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一审判决,四人犯“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不过因情节较轻不予刑事处罚。
他们被拘时,猴子也被扣押,6只猴子最终只回来5只,其中两只是鲍凤山的,他另外一只猴子、12岁的“阿丹”在扣留期间死亡。猴子遗体无法运输,他们把它埋在了一处荒山上。
鲍凤山提到阿丹时垂下了头。两只猴子回来后放在弟弟鲍庆山家,小朋友趴在猴笼前玩耍。阿丹活着的时候很护犊子,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小猴子就会攻击。阿丹还是街头猴戏表演的主角,跳舞、投篮……能演很多节目。说起它的精灵古怪和通人性之处,鲍凤山像在夸自家小孩儿。
鲍凤山说,以前从没办过“运输证”,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遇到过查“运输证”的情况。
10月8日,耍猴人通过新野县猕猴艺术协会向黑龙江当地法院邮寄了上诉状;10月16日,协会发布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辩护律师团参与二审诉讼。会长张俊然说,耍猴办“运输证”得有邀请单位,邀请单位向所在省的林业厅申请后,向河南省林业厅发函,艺人再拿相关资料到县、市林业部门逐级审核,最终由河南省林业厅审批、发证。这对没有邀请单位、路线并不固定的街头耍猴艺人来说很不现实。
张俊然担心,如果此次关于“运输证”的判决开了先河,街头猴戏表演艺人的处境将雪上加霜,对没落中的猴戏艺术传承也会不利。
后继乏人的猴戏艺术
河南省新野县曾被媒体称为猕猴丛林外的第二故乡,当地猴戏表演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2009年,新野猴戏入选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相较“非遗”、“传承”,耍猴在艺人们眼中更是一门糊口的手艺。王中续15岁出去耍猴,那些年他一年能挣千儿八百的,在生产队挣工分,到年底也就几百元钱。亲戚带亲戚,邻居传邻居,十里八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耍猴,他记忆中,上世纪90年代前后人数最多。后来,农村人可以当帮工,但一天也就挣10元钱,相比之下耍猴还是挣的多点,因此有人愿为生活忍这份苦,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丧失。他按这次出门的花销给记者算了笔账:“住30元钱的宾馆,一顿饭至少10元钱,俩人加猴子的花销,一天挣不到100元就得倒贴钱……”
“太受罪了。”鲍凤山的邻居小赵年近四十,十多岁离开学校开始耍猴,刚兴起打工热,他就离开了耍猴这个行当。打工、做生意、种地,彻底转型的人不少,现在的年轻人比当年的小赵有更多选择,有些耍猴艺人也不想让后代再承父业。
曾跑江湖耍猴的黄爱青,家在鲍湾村下辖的于湾自然村,他还记得当时村子里只有两家没耍猴,其中一家因为全是闺女。“现在?”黄爱青有点无奈,现在愿意耍猴的年轻人不多了。他后来转型办猕猴养殖场,同时训练猴子或者耍猴人。这也是如今耍猴人转型的出路。
“可能觉得不上档次吧。”黄爱青分析,年轻人都愿意和同伴扎堆去打工。他曾在村里贴出招聘启事,希望招到喜爱猴子的年轻人,培训后去景区从事猴戏表演,应者寥寥。
跟拍耍猴艺人12年的摄影师马宏杰认为,街头猴戏表演的一些节目缺少艺术性,其前景也不乐观,中国所有的文化和手艺都和吃饭有关,人们吃饭的方式改变,这些手艺就会改变或消失。如果不跟着时代变化,必然会被淘汰。同时,他对街头猴戏表演的谋生方式又抱有深切的同情和包容。“老杨说过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我们知道我们很穷,但我们出去耍猴能养活自己,就等于给国家减少负担了。我觉得这句话太有良知了。”
生活压力下的抉择
张志杰也转过行,多年前他跑到广东打工,半年才挣了1000多元钱,养不了上有老人下有读书娃的家,又回来耍猴。他感觉在街头耍猴“太熬煎了”,睁眼就得说好话,总是“低声下气的”。但像许多父母一样,他总想多挣点,给还没安置好的孩子攒点儿,“能去景区也行”。
但王中续去景区是“有条件的”。他家里有读书的孩子,还有一些农田。虽然羡慕景区的稳定和轻松,但跑江湖的自由可以让他兼顾农活儿和家里,“除非景区的工资还可以,那就把地承包出去”。其实,景区容纳不了所有人,景区内的节目要求和街头表演也有很大不同。
五六十岁是通常情况下街头耍猴人退出江湖的年龄,早年露宿街头让很多人患有风湿病,这也是耍猴艺人的职业病。“再干弄垮了身体,就是给孩子添麻烦了。”51岁的鲍凤山说。
张志久今年已59岁,靠行走江湖耍猴娶回了四川媳妇,盖起了房,养大了两个孩子。原本以为这个年龄可以含饴弄孙,可前年儿子在工地意外致残、神经受损,与建设方的劳务官司至今未了结,儿媳也一走了之,留下两个小孙子。
学话阶段的小孩子对着他们爸爸在镜中的影像含混不清地发着单音,“爸”、“爸”,歪在椅子上的爸爸则用更含混的“啊”、“啊”声回应着,倒像个更晚学说话的娃娃。“你说这怎么办,我这个年纪去打工,谁要啊。”张志久苦笑,他打算孙子稍微大一些可以送进学校时,和老伴一起,拉着儿子、牵着猴子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