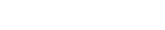禹天建绘
目前,一些地方简单挪用传统的分级分类标准进行注册许可评价,还有一些地方竟然定出每年需评出的各级别幼儿园的数量指标,并要求幼儿园大面积地参加优质园评价,却鲜见以评价结果引导质量改善的具体专项措施。
由于我国传统的学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通过评价及奖惩来规范办园行为”的老思路尚未得到拓展,容易混淆不同类型评价的标准及实施过程,甚至出现为了政绩而在评价中浮夸,进而逃避建设义务的现象。
由于保教质量参差不齐、“小学化”现象仍然存在,规范办园行为、改善办园条件、提高人员专业能力等举措被提上议事日程,“构建保教质量评估体系”倍受重视,希望以质量评估为手段,建立科学导向,着重加强对师资配备、教育过程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关键因素的评估。
由此,关于质量评价的探讨或实践尝试也日益增多,包括评什么、由谁评、怎么评、怎样利用评价结果来做出决策。但在这些探讨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不对质量评价的目的加以细化区分而笼统议论,在实践中出现一系列对质量确保和提升不利的评价乱象。
目的定位不清,质量评价扰乱幼儿园提升质量的步伐
目前,一些地方试图建立适用于任何情境的单一评价体系,简单挪用传统的分级分类标准进行注册许可评价,并未认真地将那些代表“底线”的标准分离出来,构建“注册许可评价标准”,只在同一套评价标准中以分数等级笼统地对“合格”与“优质”进行区分,忽略了二者不只是量上的区分。一方面,这种做法为准入设定了某些不必要的门槛;另一方面,混杂着大量物质和人力条件的标准,误导了“优质”建设的方向,似乎优质园建设非常容易,改善办园条件就可达标。
也有一些地方在构建注册许可标准时,目的定位在“降低准入门槛,以增多幼儿园学位数量”上,在标准中并不纳入师幼比、人均面积这些重要的质量要素,却纳入至少有三个班(或称一轨)的规模标准,排斥因应人口分布而建设小规模幼儿园、方便幼儿接受教育的努力。同时,很多地方的“底线标准”只纳入办园条件、人员资质和管理制度的指标,对保教过程中伤害幼儿身心发展的行为不加明确规范。
还有一些地方竟然定出每年需评出的各级别幼儿园的数量指标,并要求幼儿园大面积地参加优质园评价,以为质量评价会自然地带动质量的提升,除了一些笼统的奖惩,鲜见以评价结果引导质量改善的具体专项措施。有些教育行政部门将质量监测评价理解为对本地幼儿园的监管手段,样本不随机抽取、信息采集过程随意、误解数据和误用数据进行机构绩效考核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扰乱了幼儿园扎实提升质量的步伐。
这些评价实践存在的问题,都源于未能将各类评价放在更大的质量体系中,明晰它们各自对“质量”确保与改善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目的定位不清,有可能使花大力气制定出来的标准及实施细则,反而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产生负面作用,还有可能导致评价中权力的滥用。
在“质量体系建设”大背景下,清晰定位评价目的
制定评价标准和程序的第一步,应该明确评价对“学前教育质量体系建设”应起什么作用。
近十年来,很多国家致力于建设一个脚踏实地、不断推进的学前教育质量体系:首先是从确保所有托幼机构“底线质量”入手,保障所有儿童在早期享有均衡的保教机会,满足他们在人身安全、健康、人格不受贬损和歧视,以及身心发展所必需的活动等方面的“最基本需求”;接着,在“底线质量”的基础上,引导托幼机构向“优质”方向持续努力,促进托幼机构与家庭相互协作,不断改善幼儿发展的环境,为幼儿提供高品质的学习经验,而且“优质”的价值标准随着对人的发展的理解不断深化、不断更新。在这个质量体系的建设中,一些国家政府不仅意识到要对每个托幼机构进行监管和督导,也意识到需要确保自己所做的有关质量建设的决策有坚实的根据,从而对儿童早期发展和国家美好未来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在有关学前教育发展的国际报告中,甚至出现了“导向质量”这个概念,与“底线质量”和“优质”一起成为国家质量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对于“质量评价”的指标内容、主体和程序、结果的呈现与使用等方面的探讨和尝试,必须紧扣上述质量体系建设不同层次的目的,才能避免成为无本之木,真正发挥“以评促建”而非“以评扰建”的作用。
在我国,参照儿童生存与发展需求建设学前教育质量体系的图景尚不清晰,对“质量”的要素和层次缺乏分析,质量建设的近期、远期目标亦不明确,这就导致准入许可性的评价、优质认证性的评价、质量监测性的评价常常被混为一谈。
三大类型评价,由谁评、怎么评、结果怎么用各有讲究
鉴于不同类型的质量评价指向不同的目的,关于评价标准覆盖的领域、要求的高低、由谁做评价主体、评价结果向谁公布等的讨论,都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
准入许可性的“注册登记评价”,应该对所有托幼机构“全覆盖”,有强制性,无漏洞;但优质认证性的评价——“分级分类评价”或“优质园评价”,不应该强制,而应自愿报名,不能拔苗助长、大跃进式地确定“优质园”的数量目标。注册登记评价标准中,通常主要对办园基本条件、内部管理制度进行规范,但“保教过程质量”的底线指标不能排除在外,也就是关于“禁止做”与“必须做”的规范,如涉及人身安全的校车接送程序和紧急事件处置程序、涉及身体健康的代服药程序等的情况应明确。优质认证性的评价则应主要聚焦保教过程的特征,对条件的考察需紧扣保教过程的需要。“儿童发展状况”作为“结果质量”指标,理应纳入到质量监测性的评价中来。但是,幼儿园的分级分类评价就不宜将其纳入,否则,就意味着幼儿园有可能因“生源”的整体背景,而在评价中处于不利或优势地位。
在由谁做评价主体方面,由于“底线质量”可以根据妨碍儿童合法权益的消极行为明确界定,而“优质”标准则可能因教育价值观的差异,允许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并不断变化,因此,与准入许可性的评价需要由政府部门做评价主体不同,优质认证性的评价更适于由专业组织来进行,有助于优质实践的百花齐放。
从评价结果向谁公布来看,质量监测性的评价要求样本具有地区代表性,所以不能任凭某些机构自愿参与,而要随机抽取,但为了保证获得真实的数据,历次数据只能从整体上发布,不能透露具体机构的信息,更不能对评价结果进行排名甚至问责;而优质认证性的评价为了倡导“优质”的理念,也为了促进质量提升,则要向社会公开详细评价结果。同样,准入许可性的评价,也应向社会公开单个机构的评价结果,保障家长在选择机构时的知情权。
由于我国传统的学前教育行政管理体制,“通过评价及奖惩来规范办园行为”的老思路尚未得到拓展,容易混淆不同类型评价的标准及实施过程,甚至出现为了政绩而在评价中浮夸,进而逃避建设义务的现象。在建设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新形势下,有必要明确层层递进的质量体系所需要的不同目的的质量评价,使各种类型的评价真正实现其定位的目的,合力为学前教育质量的确保与提升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