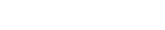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不定哪天就撂半道儿啦”

老人在早市卖菜。微信朋友圈截图
从村屯到早市再回到小屋,一路上总有人默默接过菜袋。这个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偶尔“沾沾自喜”:“人缘好,人家才给扛菜吧”。
20平方米、黑洞洞的小屋里,满是呛鼻的酸腐味儿。炕上堆着黑咕隆咚、分不清是被子还是旧衣服的一坨坨儿,与落满厚厚尘土的纸壳混在一起,引来几十只苍蝇“嗡嗡”乱飞。圆桌上堆满了碎边的茶杯、小锅和奶粉,敞口的月饼袋里,几只苍蝇跌跌撞撞发出“唰唰”响声。
在道外区民主乡光明村天理屯,老人住的小泥屋像个破鸭棚。屋外是泛黄的小菜园,老人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从泥土中钻了出来。
她与50多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儿子的身体孱弱,只能偶尔打点儿散工,常讨不到工钱。全村人都知道,这个上百岁的老太太,要用每天卖菜的钱贴补家用,给自己买最便宜的降压药、救心丸和胆囊炎止痛药。
月饼、奶粉、几双旧鞋和衣服,都是附近村民硬塞过来的。老人显得惆怅:“好人多啊,比儿子闺女还孝敬我,高兴呐,总觉得都不是我的”,她递来身份证与掉页的户口簿。上面记录着她的名字:刘白氏,1911年出生。
白天择菜,傍晚为30多斤豆角、茄子和香菜打捆,常常要打到半夜。凌晨3时起床,没有洗漱也没有早饭,老人摸黑迈出家门,拖出一只袋子,走十几米,放下,转身将第二只拖到第一只的位置,再继续向前拖第一只,如此反复——从家到公交站只有200米,她整整挪了半小时。
细心的村民和早市上的好心人发现,老人的菜袋今年明显小了。一路上,村民和民警从老人手里“夺”下菜袋,开始了每天200米“接力”,护送老人蹒跚坐上公交车。车上,乘客们为她占到一个不太颠簸的座位,在漫长的一小时车程里,纷纷伸出手,扶住老人的肩膀和她怀里的菜袋。
好心的公交司机免去了3元车票,偶尔一边开车一边“埋怨”:“这么大岁数了,别扯了呗”,老人动动身子,显得十分过意不去:“说不定哪天就撂半道儿上啦,嘿嘿”,她伸长脖子,对着司机的后脑勺,露出“讨好”似的笑。
她的记忆渐渐空白
她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丝毫不似村里那些上了年纪、整天找乐子的老小孩儿。百岁母亲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洞,深不见底。
老人的“午饭”,通常是牛奶和着饼干,在下午两三点钟对付一小口。她的记忆越来越差,眼睛也渐渐不听使唤。
粗糙的记忆大体拼凑出这个山东女人艰难的一生:1959年,她与丈夫带着大女儿来到哈尔滨,在屯里落脚。她还有3个儿子,一个意外事故,一个死于肝硬化,一个被绞死在砖厂失灵的机器。现在,她已经记不清儿子是哪年生的,又死于哪年。她一边回忆,一边皱紧了眉,最终虚弱地闭上眼,摇摇头,垂下肩: “记不清了”。
那个依然在世、与母亲一起拥有最长时光记忆的大女儿75岁了。刘白氏曾把她几乎全部积蓄借给外孙,希望他赡养母亲。一年前,她还曾在卖菜后一路摸到大女儿住的养老院。后来,大女儿被外孙换到另一家,从此与刘白氏“失联”。
从光明村、东风村到太平桥,十几年来,菜卖得越来越远。白天,她偶尔独自坐在村头,偷偷掉下泪来。“想孩子了。”村民们猜,“死的死,指不上的指不上,见不着的见不着”。
她甚至忘记吃饭。坐在早市里,她掰着手指头用力念叨:谁买了她的菜不让找钱,谁帮她背袋子,谁帮她卖苞米。
崔爱喜逗她:“‘黄金钩’又卖出多少呀?”她一脸迷茫:“忘了”。
“黄金钩”对刘白氏来说,像金子一样珍贵。她竟忘了。
时光倒转回4年前。崔爱喜至今依然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帮老人叫卖那天清晨,老人的菜第一次卖光,兴奋不已。老人的脚边却留着一堆“黄金钩”,任多少人提出要买,就是不肯卖。
收摊前,老人弯下腰,把这堆“黄金钩”一捧一捧装进塑料袋,捧到崔爱喜面前。
“我自个儿种的“黄金钩”,好吃,谢谢你帮我”,老人仰起布满皱纹的脸,又露出了那“讨好”似的笑容。
崔爱喜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