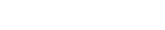精神家园
快速发展的大潮面前,一个时代性命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城市化浪潮中还要不要守护农耕文明、建设乡土文化?
如果上溯三代,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农村人。一个人无论走多远,故土乡情,承载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渔舟唱晚、野渡舟横、老树昏鸦、夕阳西下……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故乡的永远最美好。
2012年4月,84岁的余光中受聘北京大学时说,回忆起故乡的一朵花,一棵草,一块石,一片云,都可以让我们远离尘世的冲突带来的痛苦,让脆弱的心灵享受片刻的安宁。乡愁如滴水穿石般征服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最后化作丝丝缕缕的独特的乡土情结。
“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流水冻了,我在河畔等你……”余秋雨这段缠绵悠远的文字,更是道出了每一个中国人灵魂深处渴盼的寻根冲动。
“乡村的美景让你双眼舒服,清新空气让你心情舒畅,这里的人不会给你压力,不会说假话,回到乡村,就找到了根、找到了魂。”出生在天目山脚下的刘柏良在机关工作10多年做到处级干部后,毅然辞职做一个专职摄影师,回到小时候当放牛娃的村,并立志走遍浙江的山山水水,一村一村寻访,一山一水眺望。
“曾几何时,人们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为荣,跳出‘农门’便是有出息。”刚过知天命之年的刘柏良说,但家族的延绵、祖宗的祠堂、年迈的父母,还有在农村、在故乡那一份情结,是永远割舍不了的牵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最高领导人响亮而明确地回答了这个时代命题。
浙江在实施“千万工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强调要差异化建设,因村制宜,与城市的时尚、集聚、繁华相对,农村要突出生态、宁静、美丽,要有桃花源式的意境。提出农村一定要姓“农”,要有农村的风貌、风味、风景。
2004年召开的第一次“千万工程”现场会,在湖州的赵湾村,村庄整治没有拆房子,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造、规划、建设,杂乱无章的垃圾村,规划后变成了错落有致、又有文化气息的美丽村庄。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
“山、水、乡愁”,这样诗一样优美的文字,出现在中央的文件中,给人以无法言语的激动。
“回到村里、站在村头,感觉很踏实,有落叶归根的感觉。城市里的钢筋水泥房子再现代、再漂亮,也不是故乡。”在城市工作生活大半辈子,70岁的周富春执意回到家乡。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耕田读书。”这是一幅普通村里人家的对联。
“世间千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乡土中国的家风。天南地北、海角天涯,只要是有中国农民的地方,“耕读传家”四个大字一定顶在门框上,“忠孝节义”的教诲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耳熟能详。
渴了请你喝碗水,饿了请你吃顿饭,难忘的乡音、厚重的家风、淳朴的民风同样是风景。
徐秀梅是苍坡村的“活史书”。“村里南寨墙上有一座望兄亭,与南边方岙村的送弟阁遥遥相对。”徐秀梅说,当年李氏苍坡村七世祖李嘉木、李秋山兄弟夜夜畅谈,为了确保来访的兄弟安全到家,他们相约,到家后在村口亭子上点一盏灯笼。
“看看望兄亭,老祖宗是怎么做兄弟的!”苍坡村民教育子女,就这一句话。
提倡“义利并重”、被奉为温州商业精神圭臬的叶适义学祠人来人往。徐秀梅说,不管在外多远,望兄亭、义学祠是苍坡人共同的挂念。
“传统文化、精神家园,需要一种仪式和庄重感。”一位专家说。民间的努力和官方的导向开始合流,旧祠堂、古书院、大会堂、闲置校舍和文化活动中心被开发出来,成为具有仪式感的农村“文化礼堂”。
“我当书记20多年,从没碰到过一件事情全体村民无一反对,文化礼堂破了这个例。”慈溪市崇寿镇傅家路村党支部书记陈沸沸说,在农村,教会有教堂,念佛有佛堂,大户人家有祠堂,我们应该建文化礼堂。
孝悌榜、学子榜、寿星榜……行礼的礼堂、学习的讲堂和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公共文化生活重新在农村萌发。
文化礼堂为农民打造精神家园,让他们在“身有所栖”后“心有所寄”。
亮丽的风景、美丽的村庄、富足的心灵、悠长的余韵……悄无声息,你已经打上乡土故乡的烙印,夜深人静,心头浮现出故乡的落雨、小溪、青石板……
“弯弯的小河,青青的山冈,依偎着小村庄。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这是“一生最大的遗憾没能回大陆”的邓丽君演唱的《小村之恋》,这首清新脱俗的思乡之曲,被不少海内外华人誉为“宛如天籁,是梦里的呼唤”,拨动无数游子的心弦。
故土的召唤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人奔向乡野去感受乡愁,寻找乡约,重温乡恋……
寒来暑往,村庄静静伫立,没有言语,等待一批批游子归来,治愈一颗颗浮躁、疲惫的心灵。

浙江德清县筏头乡“裸心谷生态度假村”以低碳理念兴建的“森林度假夯土小屋”建筑群(2012年6月2日摄)。新华社记者谭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