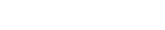老师刘保生在为学校唯一的学生上课。


林州西北,“北雄风光最胜处”的太行山横亘于此,群峰秀拔峭壁险峻,是许多旅游爱好者和写生者的钟爱之地。
高家台希望小学就坐落在太行山深处,学校鼎盛时期有60多个学生、10多名老师,响彻山谷的朗朗读书声曾是叫醒大山和世居于此居民的“闹钟”。时光荏苒,随着年青一代走出深山,学校日渐式微,到如今,学校只剩下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和一座空寂的院子。
一个学生的学校
黎明前的大山深处,山如剪影镶嵌在夜空中。
崔随娣起了个大早,在地里转了一圈回来,半山腰上依山而建的学校还没有开门。
很多年前的这个点,学校早已经亮起了灯光,朗朗读书声响彻山谷,像个“闹钟”,叫醒沉睡的大山和世居于此的人们。
崔随娣晃了会神,天色渐亮了,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出现了两个身影,一大一小,一前一后,“刘老师他们来了!”崔随娣看着身影说。
这是个周一的早上,和其他学校不同,这里没有唱国歌升国旗仪式,只有一个孤独的身影,捧着课本早读——声音清脆单薄。
高家台希望小学建于1990年,由当地村民捐款和政府拨款共同建造。在上世纪90年代学校最鼎盛时期,有七个年级:学前班到六年级,60多名学生、10多名老师。
现在的校园,一片清冷,当年村民集资捐建的教室大门紧锁,有些门上的锁也锈迹斑斑,窗户台上一层厚厚的灰尘。
2012年,刘保生被调到高家台希望小学的时候,学校还有5个学生:3个一年级,两个学前班,崔随娣的孙子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夏天,一年级的学生升至二年级后,就转到了乡里最大的学校——距此几十里外的郭家庄中心学校。
仅剩的两个学生,一个跟着父母去了别的地方,一个就是秦靖桅。
一位老师的坚守
刘保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家住石板岩乡石板岩村西湾小组,1977年,高中毕业两个月后,刘保生被村里聘为小学老师,至今已经过去了37年。
在那个人民公社年代,“教一天课等于一个工,10分,相当于一天几毛钱。”刘保生说,“到了月底,公社还会另外补助两块钱。”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神州,“工资由村里支付,一个月50块钱”,直到2004年,刘保生才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石板岩乡位于林州西北部的南太行山深处,“奇山峻峰,群峰峥嵘,阳刚劲露,一派气势恢宏的北方山水风光”,早些年间,这样的说辞也只是这个太行山深处乡镇条件“艰苦卓绝”的注脚。
37年的老师生涯中,刘保生的足迹几乎辗转过山里所有的小学,在他的印象中,大多的学校都是“一到五年级,一个学校四五十个学生”。
其实,他也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就这样变少了。在他记忆的深处,2001年左右,明显感到乡村的学生人数锐减,有些乡村小学“仅有四五个学生,一两个老师”。
“山里穷,孩子长大了娶不到媳妇。”刘保生说,为此,很多家庭想方设法搬出了大山,走进了城市。他坚持认为这是当地学生锐减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私塾般的教与学
“骑,骑车的骑,马字旁,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可。”刘保生站在讲台上,用教鞭指着黑板上的字,加重了口音领读。
教室的中间,几张桌子拼凑在一起,秦靖桅孤独地躲在桌子背后。
虽然只有一个学生,每天早上8点,高家台希望小学也会准时开门,按照既定的课时表,每天七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三节,语文和数学穿插教学。
“有时候也会整个上午学语文,下午学习数学。”刘保生说,学校条件有限,平时都是自己出题或者利用资料对秦靖桅进行辅导,期中、期末小靖桅则要到郭家庄中心学校参加全乡的统一考试,“春节前,他全乡统考第一”。
念着课文,秦靖桅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拖沓,刘保生敲了一下桌子,“休息十分钟,踢球去”,孩子立马来了精神头,抱起足球就跑了出去。
“以前的时候,学生多,提个问题也是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看着跑出去的秦靖桅,刘保生摇着头,无奈地笑着说,“现在就这一个学生,有时候教的也没劲,学的也没劲,主要还是没竞争!”
课间休息时,师生两人主要的课余活动就是踢球,秦靖桅喜欢当前锋,通常都是他主攻,老师防守。两个人,你来我往,玩得不亦乐乎。
秦靖桅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时光,因为终于“有人陪我玩了”,他说可想快快长大,因为长大了就可以“到郭家庄中心学校上学了,那儿可多人呢”。
刘保生办公室后面是一片菜园,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扛着锄头整理整理土地,种点蔬菜,自给自足——刘保生家距学校8公里,山路崎岖,每天往返并不现实。
周一来校时,他都会从家里带足一周的伙食。放学后,他就变身“大厨”,给自己烹制一桌饭。“下雨下雪了,孩子回不去了,我们俩就一块做饭,一起吃。”
通常到了放学时间,秦靖桅的家人就会过来接他,如果家人临时有事不能来接孩子,刘保生就骑着电动车,把孩子送到两里地以外的家中。(记者王战龙/文白韬/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