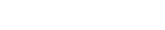当事物的表象与其本质全然分离乃至对抗的时候,俗世沉浮的众生能否参透这镜花水月般的迷离色相?不由得想起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相形之下,如何勘破这繁华缱绻背后的狰狞,怕亦是当代人面对的巨大道德挑战。
此次北京戏剧奥林匹克,莎翁经典的当代阐释不少。遍观各剧,来自格鲁吉亚阿巴希泽音乐戏剧院年轻导演大卫-多亚什维利的《麦克白》深得我心。
导演进行了颠覆原作的全新阐释。剧中很重要的改动是对邓肯形象的处理。原剧中的邓肯宽厚贤明,到了舞台上变成一个欺男霸女的龌龊老头,他侮辱臣属,凌虐儿子,前往麦克白城堡时面对柔弱美貌的麦克白夫人表现得如同性虐狂。被弑的君王被处理成暴君、小丑。相应地,麦克白杀邓肯前的台词“这个邓肯秉性仁慈,处理国政从来没有过失,要是把他杀死了,他生前的美德,就要像天使一般发出喇叭一样清澈的声音,向世人昭告我的弑君重罪”也被删除殆尽。
这样的阐释有依据吗?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在历史学家赫林谢德的《英格兰编年史》中邓肯就是个暴君。他谋杀自己的继承人,入侵麦克白的领地,终被麦克白杀死。莎翁的戏说本身就在阐释中改写了历史,导演的舞台呈现将其颠覆并无不妥。对观众来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颠覆究竟意图何在?
剧中麦克白夫妇一个挺拔清秀,一个窈窕婀娜,显得单纯柔弱、温存多情。就连谋杀犯罪的时候他们都那么无害、可人。一只靠枕轻轻捂住邓肯口鼻,倒是暴君的死丑陋而狰狞。杀人之后,一对璧人被举入空中,在迷离光影和缠绵歌声中相互爱抚。就连最终走投无路而死时,他们也是手拉手饮下忘川之水,躺在彼此怀中恬静入眠。
难道导演想要挑战我们既有的道德观念?绝非如此简单。一边是温柔缠绵的璧人,而另一边,弑君篡位的麦克白同样罪恶昭彰。与原作相比这罪恶被强化放大。他的牺牲者,麦克德夫的无辜妻儿在舞台上反复出现,控诉他的血腥和暴虐。呼应着麦克白的凶残,女巫也不再是操弄世人如傀儡般的超自然力量。她们时而是谋害班柯的杀手,时而化为麦克白朝中唯唯诺诺的廷臣;时而是临危自叹的麦克德夫夫人,时而又变做宫中御医,不是来治疗疯癫的麦克白夫人,倒是替麦克白念完他穷途末路时那段独白:“(人生)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当一切尘埃落定,她们登上高高的脚手架,鬼魅般挑衅而优雅地吟唱:“吾等何处再相逢”,剧情在终结处轮回至起点。
这是个令人难忘的舞台世界,作恶者的模样如此天真单纯,而罪恶造成的恐怖和苦难依旧震撼人心。连冥冥中的神力也化为人心恶念及其所造罪业,弥散于尘世间。最终,作恶者被恶行吞噬,人们为其选择付出沉重代价。
这舞台阐释看似乖谬费解却深得我心。莎翁写麦克白,着意于叹惋那被罪恶引向毁灭的高贵灵魂。而在格鲁吉亚导演的阐释中,罪恶虽把人世变成地狱,造恶者本人却仍显单纯、美丽、无辜。我们眼中所见是谋杀场景,耳中听闻却是清新缠绵的歌声。偶像男女一般的麦克白夫妇,像是浪漫爱情悲剧的主角。所有的舞台节奏、气氛都在引诱观众移情于这对天真无邪的小儿女。但所有熟知剧情的观众都无法被这罗密欧和朱丽叶般的舞台视像裹挟而去。这是一种极独特的舞台经验,我们一边沉溺深陷,一边抗拒逃离。当事物的表象与其本质全然分离乃至对抗的时候,俗世沉浮的众生能否参透这镜花水月般的迷离色相?不由得想起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相形之下,如何勘破这繁华缱绻背后的狰狞,怕亦是当代人面对的巨大道德挑战。
在演后谈中,导演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如果罗密欧和朱丽叶能活下来,幸福地在一起的话,他们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今晚的《麦克白》。诚然,在我们的后工业时代都市生活中,公开赤裸的罪行并不多见,一切都被包装得单纯而无害,甜美清新是人们自然而然的生活姿态。在这样的时代如何讨论恶及其相关的道德主题?年轻导演的舞台视像处理了这一悖论,拉近了莎翁与我们的距离。
这出《麦克白》在舞台视觉上动了脑筋,导演对演出的阐释和理解也因为舞台造型的丰富、准确而被呈现得血肉充盈。舞台前部是一块方形平台,上面摆着几条长凳,而舞台后部则竖起脚手架。演员搬挪长凳,或在脚手架上攀爬,变换出丰富的调度。脚手架和正方平台之间是一幅可升降白屏,用来隔断空间、播放视频,或投射各种灯光效果。据导演介绍,按照原设计表演区是整个悬空的,演员走位必须极度精准,才能保持整个舞台的平衡稳定。这寓意着一失足成千古恨。遗憾的是,因为某些原因,此次演出只能将演出落实在舞台地面上进行,演出的视觉呈现乃至导演意图都因此打了折扣。
在整个舞台造型设计中,灯光无疑是最复杂的。不断变幻的灯光时而像晚会甚至KTV,营造着过于甜俗的温馨浪漫,时而又把冷硬或血红的强光刺向观众席,将之前制造的浪漫幻觉破坏殆尽。有观众看戏后吐槽,称灯光的使用毫无逻辑,是人神共愤的晚会审美。窃以为,这晚会审美般的灯光是有反讽的,只不过这层反讽意图被巴洛克般的舞台形象重重包裹,观众或许得经过几番迂回方能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