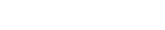忍受着雨林生活的单调、孤独和辛劳,黄卢标和他的七位队友在这里常年值守,默默地守护着世界上仅存20余只的濒危海南长臂猿,他们中守护时间最长的11年,最短的3年。
山中“飞毛腿”:“这里的山路是跑出来的”
在山势陡峭、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中,这支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的护林队下沟、爬山如履平地。只要听到长臂猿的叫声,在第二次鸣叫停止之前一定能赶到长臂猿所在的树下;只要上山,一个星期至少有两三次能看到长臂猿。
这些护林员都有双重使命,一是护林,防止盗伐;二是跟踪监测长臂猿的数量和生活习性,收集数据用于科研。“追长臂猿必须跑,这山上的路,不是走出来的,是我们跑出来的!”护林员邹正冲说,要找到这些行踪不定的雨林“精灵”,护林员必须早上5点爬起来,靠捕捉长臂猿的晨鸣,来跟踪找到它们。
41岁的黄卢标在护林队员中“跑山”速度最快,据测算他能在雨林里一个小时跑40公里,即便如此,他也经常是跟踪到下午3、4点才能回来吃上“午饭”。饮食不规律,加上常年睡在潮湿的雨林中,他和队友都患有胃病和风湿。
“你看,这里有能睡觉的木板炕,还有厨房,其他几个站都没有这儿条件好。”黄卢标说,监测站主要供护林员露营,没有电,因为潮湿也不能存放东西,他们每次进山都要背上几大包生活用品和几天的食物。
雨季是护林员的噩梦。雨林里没法穿雨衣,他们经常全身被淋透,山路又滑,遇上狂风闪电,还要随时防备突然砸下来的大树;冬天,雨林里昼夜温差大,晚上只能用火盆取暖,下半夜木炭燃尽了,大家被冻得哆哆嗦嗦……
“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长臂猿生仔,长臂猿很难人工繁殖,比大熊猫还要精贵呢。”邹正冲说,随着村民保护意识的增强,现在几乎没有人砍树和偷猎了,之前海南长臂猿不到20只,现在能够监测到23只以上。
从伐木工到护林员:“偿还一辈子的感情债”
“长臂猿跑那么远找不到吃的,我的心里很痛。我连做梦也想,这山上长满了大树。”已在雨林里守护了10年的护林员韦光说。
在监测站,韦光会习惯性地将饼干袋、矿泉水瓶收集在一处;在山上巡护,无论什么情况下垃圾都要带回来;雨林中的一草一木,连砍一棵小树都不行……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但因为常年从事护林,韦光的环保意识很强。
“有一次,从北京来了一个工程师到监测点,吃完东西乱丢塑料袋,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让他捡起来,工程师觉得很愧疚,最后捡起来了。”韦光自豪地说。
然而,让韦光难以启齿的却是20年前的一段伐木经历。当时为了发展经济,各地都开荒种地,韦光自1993年起整整砍了6年的树,那时一天最多能伐三四十棵,最粗的直径达两米。
“现在想起来就难受,这种债一辈子都还不完。”韦光后悔地说,砍伐过的地方很荒凉,再长出的树和原始林差别很大,再恢复也需要几百年,而高大茂盛的原始林,正是习惯树栖的海南长臂猿赖以生存的地方。
韦光一只眼睛因伐木受伤失明,加上常年跑山身体吃不消,他曾在2008年退出护林队,休养了两年后又归队。再次见到长臂猿,韦光激动地在心中念叨:“老朋友,又来看你了,你还好吗?”
寂寞的坚守者:“活到走不动,都要一直干下去”
“一缕月光偷偷照射过那茂密的树林,夹着夜晚那一丝雾气,像是一片轻纱,轻轻的托在那漆黑的树林里,因为有了它,夜晚的树林不再是黑暗的……”
这是护林员周照骊写给自己的一首诗。
不怕一天翻几座山的辛苦,也不怕跑山一天下来没有热饭吃,最让护林员熬不住的却是雨林中的孤独。每当夜幕降临,雨林被漆黑笼罩,护林员只能早早躺下,聊天聊到无事可聊,或者听雨林中单调的虫声、蛙声、溪流声……
从事护林11年,最让周照骊难以面对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他的第一孩子出生时,他正在雨林中追踪长臂猿,家人直到三天后才联系上他,电话另一边妻子早已哭成泪人,而第二个孩子出生,他也是匆匆从山上赶回家。
“做护林员时间久了,会积累太多矛盾,来自家庭压力很大,除了身体上的考验,还要能够承受孤独,对这份工作首先要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周照骊说。
因为工作辛苦,护林队很难吸引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加入,护林队的8位队员都不是专业出身,但通过监测和自学,他们个个都是长臂猿专家。
黄卢标对记者说:“我老婆问我,付出那么多,还得了一身病,为什么还这么卖力?我就说,海南长臂猿是这个世界上灵长类中最濒危的动物,我有责任来保护它们,活到走不动,都要一直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