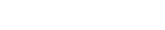路南村,浙江仙居县一个仅两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却产生了一个古往今来人们所钟爱的成语——沧海桑田,意指世事发生极大的变迁。
据晋人葛洪的《神仙传》载:东汉仙人王远在门徒蔡经家遇到了仙女麻姑,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妹妹。麻姑在姑余山修行得道,千百年过去了,长得仍如十八九岁的姑娘,秀发垂至腰际。她说:“我自从得到天命以来,已经三次见到东海变为桑田。”
成语中涉及的这个静静的山村,今天依然坐落在浙南括苍山下、永安溪畔,沐浴着千年前的清风明月。但新千年以来短短的历史瞬间,它和同在东海边上另外3万多个浙江村庄一样,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落后、污染、肮脏到繁荣、洁净、美丽的蜕变过程。
沧桑巨变,换了人间!

往日臭气熏天的浙江省嘉善县北鹤村的小河如今已经清澈(摄于2014年4月11日)。新华社记者王定昶摄
乡愁安在
浙南温州的永嘉县处于雁荡山麓,域内楠溪江蜿蜒向东,沿江的古村默然矗立,山山水水间,还留下了谢灵运、王羲之等文化名人的隽永诗篇。
今年已是85岁高龄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接过老师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衣钵,他的研究重心,就是中国的古村落。20多年前,他来到楠溪江畔。
“古村既极其朴素粗蛮,又极其精致细腻。没有看不尽的雕梁画栋、琐窗网户,全是原木蛮石,几乎不加斧凿。”
这些房子里还住着亲切、温情的人们,房屋大多只有矮墙短篱,村民们往往互相从墙头篱端递一碗酱、半瓶酒、几棵葱,老人家的寒腿好一点没?做年糕的糯米备够了没?没有一个村里人会被遗忘,会被冷落。
然而,世纪之交的一把火烧出了永嘉古村落保护的困境。其时,枫林古镇圣旨门街失火,镌刻着皇帝嘉奖当地乡贤圣旨的古拱门烧毁了。
“烧得好!”当地有人说。陈志华想不通。村民告诉他,因为有圣旨门,所以农民没办法建新房、住新屋。永嘉农民赚到钱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建新房,过个春节,老房子就不见了;莫名其妙一把火,千百年的留存就成了灰烬。
陈志华为此奔走呼号:“留下吧,留点吧,留一个吧。”
10多年前陈志华再去。鹅卵石铺的地面,变成了水泥路;村口古塔的砖头,成了农民门口的垫脚石;左折右拐、豁口不断的长廊,现在一气贯通,挂上了大红灯笼。
当地一位县领导请陈志华吃饭,他竟然在饭桌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没了!没了!全没了!”……
眼泪似乎是失落的祭品。60多年前,梁思成目睹化为断壁残垣的北京古城墙,洒下了泪水;几十年后,他的弟子陈志华看着疾速消失的浙南古村,同样流下了眼泪。
新房子住上了,但文化沉淀却找不回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还有大量城市周边的乡村。浙北嘉善县在城市化进程中已消失了126个自然村,星星点点的村落被复垦成耕地,看不出一丝人迹。
嘉善地处杭嘉湖平原,一马平川。77岁老人曹永才说,城市、工厂越来越大,村庄的地方越来越小,自家的猪圈已经变成工厂。“只有原来的村庄消失,农民才能住进新房子。”
曹永才说:“我们平原上的房子,就像韭菜一样,十年一茬。”
在城市化、工业化大潮面前,更多的村庄失落在凋敝之中。
“许多村庄难逃衰败的命运。”作为一名曾经的“学者型”官员,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委员顾益康几十年始终不懈为“三农”呼吁。
农民富起来了,但是农村环境“脏乱差”长期没有改观,农家小洋楼和露天粪缸并存、生活污水直排门前小溪,这样的情景,在上世纪末的浙江农村随处可见。
如今已是“美丽乡村”示范点的桐庐县环溪村,以前村里有句顺口溜: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刮,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溪沟就是垃圾污水的家。
“掏空村庄的还有人员外流。”遂昌县大拓镇大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巧会说,前些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庄如同房子,没人住,一年两年,便衰老、没有生气了。村里遇到红白喜事时,敲锣打鼓半天,凑不齐来暖场的村民。
工业化、城镇化如同脱缰的野马,在广袤的农村肆掠而过,更多的人在思考、在追问:乡愁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