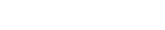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首先撇开社会上弥散的一种“公益就是骗钱”的诛心论,从中立的角度去理性分析。首先,作为一个公募基金,我们既要看到它对社会承担的公共责任,也要承认它的自我决策权,尊重它在其服务领域的专业判断。一个公募基金,是否在唇腭裂救助手术中增加美容和心理辅导的项目(从而让孩子能更好地融入社会而不仅仅是恢复器官功能),是否选择和私立医院(包括美容医院)开展一些合作,是否支持专门治疗唇腭裂儿童的专业公益医院的发展,都应该获得充分的尊重——只要这种决策不违反基金对公众的承诺,符合基金的宗旨,通过既定的程序合法作出。接下来,公募基金在作出相关决策时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才是公众监督应该考虑的核心。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采取理事会这一集体决策机制,同时规定,基金会理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这一规定的落实才是本次争议的最关键地带。
在质疑方看来,李亚鹏作为嫣然基金的灵魂人物,通过决策将善款捐赠给自己开办的嫣然医院,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需要回避。在李亚鹏看来,他也觉得非常委屈,一方面因为嫣然医院不是私立医院或营利组织,而是民办非企业组织,受到民政局的监管,不存在分红赢利的问题;另一方面,嫣然基金只是红十字基金会监管下的一个计划,本身不足以构成基金会这一法人主体,也就没有嫣然基金理事会的日常运转和决策回避制度。既然并无违法之处,又何来利益输送之说?所以,双方的根本争议,并不在于哪一方是正义的揭露者,哪一方是邪恶的侵吞者,而是我国的公益法律规定落后于大众理想这一现状所造成的。如果我们的慈善立法能够覆盖到这些不具备法人资质的公募基金或计划,或者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能够敞开大门给予更多的善事团体以公募基金会的资格,那么今天的这个争议完全可以迎刃而解。嫣然基金将有义务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内部治理程序进行管理,而李亚鹏也应该在基金是否资助嫣然医院这个问题上回避。在避免了利益冲突之后,基金会作出的决策将有助于其他更多的医院参与到与嫣然医院的竞争中,既促进嫣然医院提高自身实力,也利于嫣然基金更有效率地使用善款。
第二个关于财产公开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和法律规定的模糊相联系。就基金会的法律规定而言,《基金会管理条例》关于向社会公众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的要求也是针对基金会整体,即应由红十字会作为囊括各个基金计划的整体公布相关材料,而嫣然基金认为自己也额外公布了捐赠明细以及年度审计报告,并未违反这一法律的规定。就嫣然医院所涉及的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管理规定,李亚鹏认为没有财务公开义务的主要依据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即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至于向社会公布则采取“适当方式”即可。这种观点可能在以前是正确的,但是嫣然医院可能没有及时跟进2014年1月1日刚刚生效的《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其中规定慈善组织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捐赠财产的来源、种类、价值等接受捐赠信息;捐赠财产用途、使用效果等捐赠财产使用信息;年度工作报告、审计报告等专项工作报告”。所以,嫣然医院需要在这方面作出改进。但是,这一规定仍然有模糊之处,即这些公开的财务信息要详细到何种程度?是每一笔开支都要列明,还是以专业机构的审计报告为主,再辅以相关捐赠信息的综述?公益组织的财务公开要求,应该更加明确和科学,既推进机构的透明度建设,接受社会监督,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到公益机构的成本,在两点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位置。而目前这样的立法,是缺位的,这也加剧了公众期待和公益机构实践之间的落差。
我国的民间公益起步甚晚,尤其在社会诚信缺失、政府监管不力的情况下,受到诸多非议,举步维艰。而慈善立法的滞后、模糊性,以及公益机构对法律变化的应对不及时,都进一步加重了公众的质疑情绪。这一局面的改善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政府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公益立法,尤其是科学制定公益组织的财务公开要求,同时放开门槛,让更多的基金会和其他公益组织涌现并形成良性竞争,包括财务透明方面的竞争;加强监管强度和财务审计机构的中立性建设,树立政府监督的威信。在公益机构方面,应对财务透明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在决策方面更加注重程序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对于公众来说,更广泛的理性质疑将有助于民间公益事业的更好成长,但也要防止诛心论的思路扼杀了这株脆弱的公益幼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