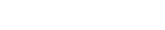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新界(HongKong NewTerroteris)位于香港地区的北部,约占香港面积的92% 。它北以深圳河与广东省深圳市分界,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烟墩山。狮子山、飞鹅山与九龙相接。图片源自网络)
夜半读碑文,愈读愈精神。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便找出碑文来读。
历史不见得非得记载于史书里,更不可能局限于正史。在香港的新界,散落着大量的宗祠、寺庙,它们都在默默记录着历史。自明清以降,很多寺庙延续了数百年的香火。不少宗族没有族谱,但是只要走进这些宗祠、寺庙,细读这里的历代捐赠者名录,一代代人的繁衍生息便有迹可循。还有大量的碑文,记载的是种种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是历史上曾经打过的官司。主佃之间因为纠纷,闹到衙门,官员宣判以后,当地人将事情经过,以及结果刻下来——“勒石永遵”。 《奉督抚藩列宪定案以仓斗加叁准作租斗饬令各佃户挑运田主家交收租谷永远遵行碑》、《公立大奚山东西涌姜山主佃两相和好永远照纳碑》和《奉列宪定行章程悉以仓斗交租给示勒石永远遵守碑》就分别记录了三场这样的官司。从这三块碑文中,我们可以管窥清代英国殖民者来到之前,新界是怎样一个社会。
在刻板的印象里,自秦始皇建立封建制度开始,到被西方打开国门为止,中国传统社会以一种“超稳定”结构存在,不进不退,似乎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和谐社会”。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如果细查地方文献,就会发现民间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调整。根据科大卫的研究,“明、清时代在华南普遍出现的宗族制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因应元末明初政治、经济及社会转变而出现的产物”(注1:谭思敏:《香港新界侯族的建构》。香港:中华书局,2012)。所以,我们必须以一种动态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传统社会。在英国租借新界前,新界就是明清以降的典型传统社会。
《奉督抚藩列宪定案以仓斗加叁准作租斗饬令各佃户挑运田主家交收租谷永远遵行碑》记载的是一个因为收租计量单位遭到篡改,而发生的主佃纠纷。从记录看,原本主佃双方有所约定,以特定的计量单位“斗”来收租,“出自主佃两厢情愿”。而所谓的“斗”,“有圩斗、官斗、租斗、各名目大小不一”,但都有确切的标记。早在雍正四年(1726)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以大斗收租”的官司。当时宣判“烙仓斗一个”作为统一准则,以平息矛盾。谁知乾隆年间事端再起,佃户邓鼎成等“将原颁仓斗一个,捏称原颁仓斗八个,遂藉前颁仓斗,混作租斗,涂改批约,希图短租”。最后县衙宣判,一切“仍照雍正四年成案”。也即是说,这是一次未成功的篡改度量衡的阴谋。而因为事情发生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该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平定金川)五月初一日“恩诏”前,犯案人员获得“免提讯”的优待。为了使后人记住这件事,所以“勒石永遵”,该碑现在存放于元朗旧墟大王古庙内,告诉我们传统社会怎样动态进行着。
《公立大奚山东西涌姜山主佃两相和好永远照纳碑》记载的这段历史,则和迁界与复界有关。大奚山,也就是今天的大屿山。元末明初,天下大乱,各种地方势力开始出现。例如在东莞,就有何真家族。何真去世后,明太祖曾经有针对性地清理何氏家族势力,处死了何真的两个儿子,株连不少人。但与此同时,新界其他地方势力,如龙跃头邓氏、太坑和新田文氏,及河上乡和谷丰岭侯氏等趁机兴起。对中央来说,地方势力的情况实则没有什麽改变,仍然威胁其统治。
于是,康熙元年(1661)清廷因为要剿除地方势力的原因而下令迁界(由辅政大臣鳌拜下令,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五十里),致令不少土地荒废。(一般认为迁界是为了抵御割据一方的郑成功势力,但近年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对抗郑氏只不过是官方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迁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瓦解大陆沿海地区的地方势力,以减少其对当时中央造成的威胁。)
待康熙八年(1669)复界之后,社会重新洗牌,遂出现了很多混乱的局面。碑文记载,康熙四十一(1702)年,“有新邑民人控田主欺隐私畆”,也就是地界搞不清楚了。到乾隆十五年(1750),发生官司,当时宣判一切如旧平息。但佃户陆续自资“或在山头地角、或在海边沙滩,工筑成田”。田主忍无可忍,乃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再度控告佃户。官府派人前去丈度田地,双方对结果皆不能接受。一直闹到乾隆四十年(1774),“主佃议和”,但“别庄有所不愿”。所谓“别庄”,竟有来自长洲甚至东莞者,可见当时的田主未必一定住在大屿山,“跨地域地主”普遍存在。再经人劝说,“主佃和好,公立合同”。最后“以立石之后,我等遵案照批,世世不朽”。该碑存于大屿山东涌侯王庙。当然,“世世不朽”这种话是不能相信的。如前所述,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时而矛盾,时而和解,时而要面对迁界这样的强权介入,游戏规则随时都要调整。
《奉列宪定行章程悉以仓斗交租给示勒石永远遵守碑》则和地方的墟市有关。墟市是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中心,百姓的生活围绕墟市展开。有资格有能力开设墟市的,通常是当地的大宗族。而因为其是大宗族,所以也就拥有某种程度的“话语权”。该碑记载的,就是县民控告监生邓炫中“大斗加收、统凶抄抢一案”。乾隆三十八年(1773),元朗旧墟“仓斗坏烂,邓炫中等将从前旧斗量收”,“佃户指为改用大斗”,于是“抗欠不交”。邓炫中带人前往讨租,“牵取牛羊作抵”,“同时邓怀德等,割禾抵租”,结果发生冲突,“砍伤陈朝发,身死”。
元朗旧墟是邓氏的势力范围,邓炫中又是“监生”,握有权力,才会发生惨案。然后官府介入,认为案件难以追查清楚,列举“若核算加减换批,各佃批帖千有余张,缴旧换新,在在需费”等原因,最后决定按照早前的宣判“以吊验批帖,加减核算,另换新批,系属折中之道,仍照原议详覆”。至于牵牛羊抵租,则因为早前的官员派人前去提案,被告未到,而官员业已离任,便再传唤原告、被告前来。原告改口,称听讼师张步高唆使,“佃户梁东远等捏控不实”。
总之,最后的判决基本上恢复到双方发生纠纷前的状况,“斗无加减”,但“必须另立租簿收幖,以免抗欠、瞒追之弊”。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结果息事宁人。为示后人,乃立此碑,存于元朗旧墟大王古庙内。
有趣的是,这块碑文的副本同时出现在元朗十八乡大树下天后庙内,其中不少语句、措辞都有改动过的痕迹。例如,陈朝发被砍死之后,原文说“有讼师张步高,唆使各佃户,控以……”这里的“控”,在元朗十八乡的版本就成了“捏”。又如,官府审案之后,原文说原告“自认听讼师张步高等唆使捏控”。到了元朗十八乡的版本,就成了“自认误听讼师张步高等唆使捏控”。再如,上文说“各佃批帖千有余张”,到了元朗十八乡的版本就变成“有千余张”了。虽然在抄刻碑文时,常常也发生错谬,这个可以理解。但如增加“误”字这种,则明显是刻意的。也就是说,元朗十八乡的版本,明显有偏袒被告的倾向。其背后的原因是不难揣度的,因为元朗旧墟虽是邓氏势力范围,但毕竟有许多租户在,公然偏袒己方会引起众怒。而于同为邓氏势力范围的元朗十八乡,邓氏大可将碑文修改,以作为给子孙看而不至于太失体面的版本。历史研究中,之所以追求“孤证不举”,就是因为存在太多这样的情况,倘若不加以比对,很可能偏听偏信。
这三块碑,分别是三个切片,告诉我们在1891年英国殖民者进入新界以前,新界居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如何。解读当然可以是多样的,不必拘泥于个别。但这三块碑无疑呈现了地方宗族的建构、清初迁界前后的社会变迁、地方社会与市场三个面向的新界社会。新界历史,与九龙和香港岛的历史非常不同。当我们笼统说“香港史”的时候,其实是不那么精准的。即便是英国殖民者来到之后,新界因为是租借,和被割让的香港岛、九龙完全是两种管治方法,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地谈论香港。如胡适先生所言,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