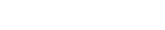毛泽东追悼大会场景
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一万五千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击。
卫生保健组的成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按照预案,治丧委员会各工作机构很快落实成立。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宣传报道组、外事组、卫生保健组等等。卫生保健组由刘湘屏(女,56岁,卫生部部长)、黄树则(61岁,卫生部副部长)担任正副组长,负责处理吊唁、追悼大会期间领导和群众的卫生保健事宜,经常参加办公的有卫生部王桂珍、黄开云、才生嘎、张立和北京市卫生局谷秀波、辛福录等六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33岁的王桂珍,她是名扬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是电影《春苗》女主角的原型,1975年刚从基层调到部里出任核心组成员,相当于副部级职位,被视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从职务上看,卫生部女局长黄开云、北京市卫生局医政组组长辛福录较为熟悉业务,应该是实际操作的具体协调人。
卫生保健组的当务之急,是9月11日至17日吊唁期间的卫生保健工作,经过紧急处理的毛泽东遗体安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估计每天有十余万群众前来瞻仰遗容。刘湘屏、黄树则根据以往经验,决定在北大厅的东大厅内由中南海门诊部、北京医院设立医疗点,重点照顾中央首长和省市领导、重要党外人士;而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文革”中被改名)、阜外医院的医疗点设在北大厅和西大厅内,主要面向一般的吊唁群众。同时,在人民大会堂外也设立四个医疗点,由北京市友谊医院、工农兵医院(即后来的宣武中医医院)、宣武医院、北医一院负责筹备。每个医疗点需要六名医务人员,其中内科医生二名,外科医生一名,护士三名,并各自配备一辆救护车。
对于参加吊唁大厅卫生保健的医务人员,卫生部首先要求政治可靠,业务上具有独立处理疑难急症病人的经验,政审由各单位党委负责,并报卫生保健组批准。因此各单位上报的名单多为党团员,都是专业经验丰富的主治医师,如北京医院的钱贻简、许国忠,首都(协和)医院的方干、华传东、宗淑杰,阜外医院的于秀章、胡镇祥等,还特别配备几名四十岁上下的护士长。像北京医院内科资深大夫钱贻简,曾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多年,与中央领导较为相熟,他在医疗点的出现会令不少上岁数的领导同志心中踏实。
为了绝对保证前来吊唁和守灵的领导同志的健康,中央办公厅和卫生保健组还按惯例安排一些医疗专家机动使用,在单位或家中待命,一旦有事由中央保健部门卜志强负责统一调遣。
张平化是唯一出险的高级干部
9月10日毛泽东遗体放置到人民大会堂后,北大厅就迎来一批批悲痛欲绝的吊唁人群,哭声震响,不少上岁数的老干部老泪纵横,步伐艰难。据卫生保健组第三期简报通告,10日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内共有61个病号,其中因悲痛晕倒19人。天安门广场内发生674个病号,其中发生一例休克,经急救后均恢复正常。
第一天吊唁带有内部性质,来的多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士,东大厅因室温过低,使那里休息的一些领导有嗓子痛、头痛、流涕等轻度感冒症状。最为严重的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他平常就患有头晕、腹泻等毛病,吊唁过后感到严重不适,医疗点大夫打算紧急安排到北京医院做脑血流图和下消化道窥镜检查。但张平化本人却要急于赶回湖南,放弃住院,搭乘当晚六时飞机返回长沙。从当时内部简报来看,张平化是整个吊唁期间唯一出险的高级领导干部。
针对东大厅第一天出现的病情,卫生保健组与中办商量后决定采取应对措施,连夜调运上百件棉大衣存放在大会堂入口处,凡是领导人士进入大堂都临时发给一件棉大衣披挂,并在东大厅内喝姜糖水。这种方法简易却颇为有效,高层干部伤风感冒的情况几天内明显减少。
一天晕倒39人
9月11、12日以后在吊唁大厅发生的病号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一些老弱病人禁受不住场面的刺激而在现场出现休克、冠心病的症状,都加重医疗点的工作劳累程度,大夫护士每天值班需16个小时以上。
这两天,广大干部群众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慈祥遗容,因极度悲痛而晕倒39人,休克一人,治疗2375人。经医疗点及时处理和精心护理,都很快恢复了正常,随队伍返回单位。(见1976年9月12日《卫生保健简报》第四期手写稿)
今天(9月12日)参加吊唁的群众队伍中发病的有2450人,其中九人病情较重,休克四人,虚脱三人,晕倒一人,冠心病急性发作一人,经过积极抢救均恢复正常。(见1976年9月13日《卫生保健简报》第五期手写稿)
今天(9月13日)人大会堂内外各医疗点治疗675人,其中留诊观察30人,晕倒12人,冠心病5人。北京市一商局政工组组长郭书印同志,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后,走出大厅后突然抽搐、痰堵,面色青紫,神志不清,经医生检查血压220、130水银柱,立即注射硫酸镁、针刺、吸氧、吸痰等急救处理后苏醒过来,内服安定片后送到北京医院急诊室继续观察治疗。(见1976年9月14日《卫生保健简报》第六期手写稿)
据9月17日晚上统计,从10日到17日吊唁期间,大会堂内共治疗398人,大会堂外天安门广场共治疗8431人,巡诊6984人,合计15813人。一万五千多人在吊唁大厅内外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状,体现出中国民众对最高领袖去世的悲恸程度和承受不住的精神打击。这么大的治疗量确是事先无法料到的,居然就靠三十多位大夫护士当场处置而圆满解决,在医学治疗史上也属一种特例。
医务工作者受到表扬
卫生保健组用“工作认真,积极负责,坚守岗位”这几句话来称赞参加吊唁工作的医务工作者,特别是在人大会堂外边,在露天作业的大夫们有时冒着炎热的天气,有时还要顶着大雨,随叫随到,来回给出现不适症状的病人送药品。身为卫生部主管领导,刘湘屏、黄树则他们看到后感慨良多,几次使用了政治性言语来表述,激动得有些前后语不搭:“医务工作者都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积极精神受到广大群众的赞扬……”
那几天数百名建筑工人夜以继日,正在天安门城楼前紧急搭建吊唁大会的主席台。人大会堂外边四个医疗点的值夜班大夫主动到工地进行巡回医疗,送去红糖姜水,并参加搭架子的劳动。9月15日《卫生保健简报》第七期记载这样一段短对话:“工人同志说,‘我们看到你们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受感动。’医务人员说,‘这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结果啊。’”这是最典型的1970年代政治用语,说者流露自然,用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刻也是恰如其分的。
每日十万多人来到灵堂大厅瞻仰遗容,空气流通不畅,气味难免混杂。头两天仅由人民大会堂医务室负责大厅简易消毒一次,9月12日吊唁结束后采用点燃消毒香的办法,但仍无法解决空气混浊的问题。13日凌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来人在北大厅东西两侧进行空气采样检菌,化验后发现并没有致病菌,杂菌数都不超过五十。这表明北大厅的空气尚属洁净,这让提心吊胆的相关领导松了一口气。
广场医疗站
紧接着的工作是18日下午三时天安门广场百万人追悼大会的繁杂事宜,实际上在9月11日卫生保健组和市卫生局就已经拟定出完整的《天安门广场追悼大会医疗救护站救护工作方案》,并获治丧领导机构批准。在方案中,拟建立医疗救护站34个,西至西单北大街,东至东单北大街,但重点还是放在天安门广场内。从东西标语塔至人民英雄纪念碑左右两侧共设14个医疗救护站,每个站设六名医务人员,其中三名医生三名护士、一名司机,由各单位自带救护车一辆。方案中明确规定,各救护站由所在医院的一名领导带队,负全部政治责任。
医疗救护工作总指挥站设在天安门红西四观礼台下,配备一辆机动车来回巡视应急。下设六个分指挥站,分别设立在公安部门口、历史博物馆西门、人大会堂东门、二十八中学门前、南池子南口东侧、原工会大楼门前,具体负责相近的几个救护站的联系工作。
有趣的是,依照多年天安门广场组织大型活动的经验,各医疗救护站多以灯杆为建站标志。譬如,马克思像后36号灯杆为人民医院救护站、列宁像后9号灯杆为积水潭医院、人大会堂西北角2号灯杆下为北医一院、人大会堂南门前14号灯杆下为北医三院、历史博物馆西北角前35号灯杆下为第六医院、二十八中门前115号灯杆下为儿童医院、方巾巷南口西侧16号灯杆下为日坛医院、南长街南口东侧62号灯杆下为复兴医院等等,灯杆醒目易找,也便于划分各自的主管区域。其它还如东、西两个标语塔,纪念碑东、西侧南北草坪也作为设站的重要标志。
各医疗站只备有一些急救药品及一般常见的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和中暑的中西医药品,再则是两张行军床、折叠床及担架,条件稍好的医院还能带上一部半导体心电图机、一两个氧气袋及保护药品的冰桶。这些就是当年北京所能具备的最好的急救家当,显示医疗条件的简陋和落后。为应对副主席台上中央领导的紧急情况,在西观礼台下也只是设几张简易病床,别无其他先进的抢救设备,由友谊医院机动小分队负责。
为备急需,卫生保健组还特意在友谊、朝阳、首都、北京、阜外等医院各设几张干部病床,并让其他综合医院有意腾空普通病床十几张,准备接受较重的病人。
三千人突然昏厥
追悼大会之前,中央治丧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再三强调要注意安全保卫工作,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卫生保健组随之要求各接受任务单位,要党委领导挂帅,办好学习班,选好医务人员,并做好政治审查工作,保证不出医疗事故。
中央治丧委员会办公室事前向各单位下发了《群众参加追悼大会注意事项》,同样要求严格审查参加者的政治面貌,登记名单,指定负责人带队。再三强调:“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和捣乱。”并规定所有人员一律不准带包,会前30分钟要列队肃立,不能随便走动。而各医疗点则要在当日上午8点30分以前进驻规定位置,并各人自带一份午饭。
为防止失误,卫生保健组在9月16日晚上还提前演练一遍,35个医疗救护点的全体医务人员准时到达工作岗位,熟悉所在区域的情况。
追悼大会准时在9月18日下午三时举行,百万人站满了广场,气氛肃穆凝重。在开始播放哀乐、全场默哀肃立后的短短二三十分钟内,不同方队的三千二百多名参加者因“心情万分悲痛”而突然昏厥,先后晕倒虚脱在地,队形大乱,引发现场一片混乱和紧张。值勤的首都工人民兵和民警来回穿梭,手忙脚乱地把病人抬送到医疗点,历史博物馆西门一带的六个医疗点一下子集中了八百多名昏厥病人,三百多名病人也送到新华门医疗点。
人手吃紧,附近的几个医疗点闻讯赶紧派来几十位大夫支援。积水潭医院、工农兵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单位参加追悼大会的医务人员,以及到场的各单位红医工、赤脚医生也主动跑出队伍,到医疗站抢救病人。(见1976年9月22日群众组织指挥组医疗救护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医疗救护工作小结》)
救护人员把地毯、被子、塑料布等铺在地上让病人休息,采用针灸、西药、中西医结合等多种办法,就地抢救了大量病人。市卫生局9月24日《卫生工作简报》还透露,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内抢救大量昏厥病人,和附近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北京饭店、历史博物馆、公安部、轻工业部、旅游局、外贸部招待所、北京邮局、西长安街邮局、大风刀削面馆、原工会大楼内的部队和附近的居委会以及居民,他们主动送水、送桌子、椅子、床板、被褥、席子,邮局送邮包袋以及浓茶、白糖等,为抢救病人起到积极作用。
追悼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明显的医疗险情,只有两名虚脱者,一般患病21人,主席台下有九名警卫战士因过于劳累晕厥。整个追悼大会过程中,医保方面无一差错,平安度过,主事的刘湘屏、黄树则为此才能松一口气。9月18日当晚卫生保健组发出第九期简报,居然已经有了翔实的救治数字,其多其细令人惊讶:“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共诊治20126人,其中巡诊4449人。主要疾病有虚脱3259人,心血管疾病35人,脑血管病3人,其他一般疾病16829人。”追悼大会之后,只有七人被安排送进医院治疗,其中有中毒性痢疾一人,急腹症一人,疑似脑炎一人,高烧待查一人,心脏病一人,休克二人。
市卫生局事后总结说,搞百万人大会的医疗救护工作,我们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总的来看,为大会配备的医务人员只有三百五十多名,少了一些。但是幸亏依赖了层层建立的群众防病队伍:“参加追悼大会的群众队伍都是按班排连队组建的,每个连队有一名卫生员或赤脚医生、红医工,他们在抢救治病方面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见1976年9月18日卫生保健组《卫生保健简报》第九期)
卫生保健组在事后小结中承认有两个存在的问题:一是在追悼大会中,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短时间内发生大量的昏厥病人,医护人员显得有些忙乱,经验不够;再则,会前没有疏通落实,救护车辆的票证问题未解决好,导致病人的转送受阻。
但是相对于规模上至百万、民情特殊的追悼大会来说,这几点问题已是微不足道。刘湘屏、黄树则他们在满意之余,向中央汇报中特意提到:“参加追悼大会的43个医疗点五百多名医务人员恳切要求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给他们安排一次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的机会。”
百万群众追悼大会的肃穆场景早已作为历史瞬间被世人铭记,“短时间三千多人集体昏厥”这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小细节,也可作为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有意味的事例,列入中国当代史的脚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