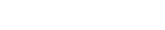据BBC英伦网报道,国外的元旦就要来临,本是一个喜庆的节日,而伦敦大学学院欧洲文化硕士廖乙臻却希望它不要来临,因为独在异乡的她始终觉得,热闹是别人的,自己什么也没有。现将其留学日记摘编如下:
走在伦敦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小广场,诺大的红色彩球串在空中,大力宣示:“圣诞节要来了,欢腾吧,人们!”空气冷冽简直像在开冰箱,可我今天穿的大衣没有口袋,于是我双手紧握,抬头盯着彩球。满天的红啊,恍惚中,一股清晰的感觉袭上。超过一年了,伦敦,我在伦敦已经待了一年多。而我知道,我是个永恒的异乡人。
英国的冬天似乎又要来了。我以一种“也罢”的淡然看待。在我心里,反正它从未离开过。
每个白天走在湿冷的路,像在横渡个什么,多数时候是一条苍白惨淡的河。清醒则在每夜。一不留神,好像无止尽也就可以这样无止尽下去。
不只一人问过我伦敦的冬天是什么样子,冷吗要不要穿羽绒衣,或是好玩吗?跟夏天比起来怎么样呢?我一律回答:“不要来。”
人类怎么能承受这种天气?试想在这里的一天内容:前一天晚上跟朋友喝了小酒(好吧,或是不少的酒。不过在伦敦不喝酒要干嘛)回家很晚所以隔天当然也晚起,因为要睡饱才能好好体验生命。
中午12点起床,心想说昨天真是不错呢过得挺爽,走到窗户前拉开窗帘,一大片灰,还有几片雨。在伦敦,多数时候不是淅沥淅沥的雨,就是哗啦哗啦的雨,不然就是滴滴答答盯叮咚的雨。
此时,开始有点被天气影响到生理地感到稍稍打击,但仍逼自己振作精神,煮了一顿饭。吃饱后泡了Fortnum &Mason(其实真的没特别好喝,但不喝它也不知要喝什么)的Royal Blend Tea,而且当然是一定要加牛奶的,配着听Pink Floyd(不要以为来英国就是要听Coldplay喔,温馨强力呼吁)。
开始觉得,对啊人生还是有希望的。来做点什么吧,看书好了。打开书,时间正是下午三点半,真是个好时间呢,我最喜欢三点半了。于是欢欣鼓舞转头看着窗外—天已经全黑。What? Come on, seriously?我的白天呢?我的一整天呢?(虽然我的一整天还在,但在全黑的天空中与我的精神里,它已经死了)
英国的冬天,永夜。这就是我给它的批注,一个前面一定要像英国人用语一样加个“天杀的(bloody hell)”的批注。我像是活在一个广大无垠被黑暗抹去了向度的时空里,一直走着。旅程中的足迹留在哪里?在一切都被覆盖中,在苍白湿冷的白昼里,在不由分说的无尽黑夜游荡中,我不确定。
我有爱上伦敦的时刻吗?有的。
那是去看了“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音乐剧的时候。表演厅比想象来的狭小,也不似法国Moulin Rouge的风格独具。然而几乎是一开头,舞台上的所有就将我置入一个强烈的迷醉时空。快结束时,座位前排一位满头白发老婆婆,低下头,以细微动作不断擦试双眼。我看到了,知道她在哭。走出表演厅,湿润的空气将街灯温暖包覆,人群吵杂迎往。我感觉到我存在。
经过我室友房间,听到她正弹奏大提琴,巴哈的Suite No. 1。房间外走廊很短,我却走了很久,也可说是几乎没在走。我像是行走在一个诗一般的梦中。
大家在UCL的酒吧喝完酒,走出去,互相拥抱。我过了街,站在对街回头望。我朋友对我挥挥手,黑暗中看得不是很清楚,只看到一只晃动的轮廓。我喊了声:“回家小心啊!”那轮廓继续晃动。
这些都是我爱上伦敦的时刻。
怎么说呢,我必须承认伦敦是有个美好的轮廓。它多元、热闹、文化底子厚,虽然有点古版呆板,人的脸也很臭。但只要莎士比亚(Shakespeare)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是英国人的一天(但他们就是,所以这永远成立)以及大本钟与西敏寺没有倒下的一天,我想人们对伦敦的幻想与喜爱就会一直屹立不摇下去。
但在这一片交杂的炙热的冰冷的喧闹孤寂的尘土之上,我总想到台北街头呼啸而过的机车声,以及阳光底下的人影,是多么热闹地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