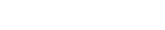民俗-黎族过年








一粒槟榔品出一个岛

海南是槟榔的主要产地。当地人有吃生槟榔的习惯。他们的吃法十分简单。首先将槟榔的尾巴切掉,这个环节看似简单却十分讲究。因为不能切掉槟榔的“头”。这个头就是从生长时与枝相连的部分。据说,此部分槟榔味最足。
在海南岛上,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卖槟榔的小摊。小摊的“组织架构”极为简单:一人、一伞、一凳、一盘、一筐、一刀、一罐、一袋。
人:多是中年妇女。
伞:遮阳、避风挡雨。
凳:供人小憩。
盘:放着新鲜的槟榔。
筐:放在地上,支着盘。筐里还有大量清洗干净的蒌叶。
刀:是特制的,像平时的方菜刀,只是小了四、五倍。
罐:装着白色的螺粉。不知情者多会以为是石灰。
袋:则是用于盛装切好的槟榔和上了螺粉的蒌叶。
海南的四周是海,海里满是海螺。海南岛上满是绿色的植物。在绿色植物上涂上海螺粉,在很多人眼里是把海放在了岛上。台湾作家欧大伟说,在台湾,也有食槟榔的习惯。一粒槟榔让人品出一个海和岛的味道。

在海南,抽烟的不多。因为岛上不产烟叶。早年上岛的外来男子会抽水烟,一品烟点一次,抽一口。男人如果不往胡须下的嘴里放些烟酒之类的东西总好像少了点什么。他们不会像女人一样,动嘴时可以家长里短地说。
在海南,成年男人塞进嘴里多是这种青葱的绿意伴着一丝海洋咸味的生槟榔。
在海南,你常会看到街边踩着拖鞋的青年男子在嚼槟榔,托着下巴,45度角仰望星空,双目小闭,此时,槟榔在口腔中正生出红汁。其中味道只有食用者自知。当槟榔成渣时,当槟榔味已尽时,食用者像谢幕的英雄一般,会吐出鲜红水和槟榔渣。
临街而立,两腮嚼动,忘乎所以,对于食用者来说实在是惬意的事。如同抽烟者香烟燃手,雾从口出时一样……
老韩是山西人,在海口呆了五年,他不抽烟、不酗酒。他很想像海南汉子一样,要几个槟榔,站在街边嚼得虎虎生威。他认为吃生槟榔时,刷在叶子上白白的东西是石灰。这让他对生槟榔望而却步。一次,和车站边卖槟榔者闲聊时,他才知道那白色的乳状物不是石灰而是螺粉。于是他果断大方地买了一颗槟榔。
老韩说,槟榔刚入嘴时,便觉得一股麻麻的、涩涩的味道通过舌头,漫布上鄂,直冲鼻腔。才几下就觉得胸口发闷,像塞了一团棉花,呼吸困难,头晕乎乎的,想吐掉又觉得口中味道有一种回甘,继续嚼,脸就开始发热,然后漫及全身,燥热却舒泰。他说这是“醉酒之外的另一种醉的滋味”。
如此说来,海南的男人吃生槟榔实在是能找到“一果在手,烟酒全有”的感觉。
一粒槟榔撑起一个家

城市、乡村和介于两者间的小镇上,海南街头巷尾随处都有卖槟榔的小摊,这是海南的一道风景线。摆摊的多是我们可以唤作“阿婆”“阿姨”的海南中老年妇女。
她们一般卖的是自己房前屋后的槟榔,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从早到晚,一天能卖掉100多个槟榔,生意好时能挣80块钱,已经足够支撑生活。
在海南,无论是雨时还是刮台风,槟榔摊都有生意,槟榔完全像油盐米一样是岛上人生活的必需品。对于这些阿姨或阿婆来说,这份收入是十分稳定且不需太多的技术和体力透支的。
现在,槟榔摊又多了些“社会功能”,那些从农村到城里来的老人多会找到摊主说上几句老家的话,念念村里的旧情。一来二去,这里又组成了另一个“家”,那就是离乡离土老人们常去的街边“老人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