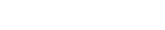(一)终结冷战思维的台湾文学研究
陈美霞:黎老师,您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里相对边缘,但是您对这个学科很有热忱。有人说您是“把台湾文学当作事业来经营”,除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外,您还很重视学科建设与年轻人的培养,近年您更是发起了多场高品质的研讨会来推动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您对这一学科的热情源自哪里?
黎湘萍:这真的是说来话长,要从我们为什么会去研究台湾文学说起。1985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不是台湾文学,而是文学理论。为什么学文学理论?1985年被叫做“方法年”,是改革开放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只是我们当时思考问题的介入点,凡是八十年代过来的人都有体会。在这样氛围下,我们的反省是:西方之外,我们的周边状况是怎么样?特别是1949年后的台湾,它的理论状况是怎样?台湾那边的理论界是不是走一条与我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会不会开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理论体系或者方法?我是抱着这样的问题去思考、了解台湾。
我的硕士导师是何西来老师、杜书瀛老师,在思想解放运动中,他们经常合作在报纸上发表文章,5个研究生中他们就让我专门做台湾这一块。我的硕士论文是梳理1949年以后台湾文论的发展,得了这个任务后我就泡北京图书馆。我早上去那里,中午就吃馒头,泡一天,找到一本书之后,根据参考文献、出版广告等,从一本书追到另一本书,按照编年的方式,做了一些研究和排列,找到台湾理论发展的方式、模式或者趋向,我自己是这样去摸索的。一开始我就把台湾文学或者台湾研究当作一个思想或理论的资源去挖掘,并没有当作一个学科。
陈美霞:我有印象您在《是莱谟斯,还是罗谟鲁斯?——从海峡两岸“走近鲁迅”的不同方式谈起》里说过把台湾文学作为一种理论批判的资源。
黎湘萍:对。两岸虽然处在分断的状况,但这是民族内部不同区域的各自发展,内在的文化脉络没有分裂,甚至在政治分歧最严重的时候都有对话。叙述民族史、文化史,一定要有整体的视野。
读博士的时候,为何继续台湾文学研究?是因为我的老师唐弢先生,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在思考重写文学史的问题。“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虽不是他提出来的,但他八十年代去香港开会时,已注意到这些问题。如何来整合一个比较完整的有着丰富生态的文学史?他认为没有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文学史是不完整的。
另外,唐弢先生还有个思考:现代文学走了这么多年,从“五四”到1949年,甚至1949年后有很多不同阶段的变化,是到了进行总结的时候,特别是在理论上进行更好阐释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唐弢先生没有精力做的事情我来继续,这既是学科的事情,也不是学科的事情,它涉及到对整个文学史的整体脉络的理解。有了这样的思考,我们做台湾、香港、澳门的文学文化研究,就有了一个基点,一种当作事业的热情和动力。
因为国际性冷战、两岸分断的结构,它使得我们民族的整体历史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八十年代是重新来反省与理解的时候。这不是宏观的空洞的,而是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做。我以前写过一篇短文,讲这个学科是最早终结冷战思维的,比冷战的结束还更早地展开了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文学对话。终结冷战思维的恰恰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边缘学科所做的先驱性的工作,光这一点我就为我们学科的人感到骄傲。
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有很多原来搞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涌进来做港台文学,貌似在“赶时髦”,其实他们已经走在通往民族和解的道路上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藏有金矿的地方,只是还没有往深里挖。我们对那些前辈、先驱者,为什么充满了敬意呢,原因就在这里,这个学科的重要意义之一也在此。有些台湾朋友有误解,问早期的台湾文学研究是不是在做统战的工作?我说开玩笑,在冷战•内战结构里,谈台湾是禁忌的问题。有了七十年代末政治上较为开放的氛围,才能保证我们讨论台湾问题不再是禁忌,保证我们能够好好地在这条路上把冷战思维的残余给清除掉。
我们做的工作远远不是学科建设这么狭义,而且我一直很不喜欢“学科建设”这个说法,因为它可能会窒息这个学科所具有的活力,特别是它所具有的寻找文学文化思想资源的活力。
沿着你这个话题延展,大概是在1988年我们文学所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后来解散,我就回到现代室,之后又到《文学评论》编辑部。2004年我又奉命出来创办新的“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这时候我就必须关心学科的问题。我做的第一个事情是开会,我把在北京做台湾研究、关心台湾问题的人请来,包括台联、台盟、国台办的同行。04年正好大家对“文化台独”很敏感,我记得会上有朋友说“台湾有些人把台独当作一种事业来做,我们大陆如果没有人把反台独也当作事业来做,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事做好。”这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政治意味很强,但是说明要把台湾研究当作一个学术事业,一定要投入热情。
我们对台湾的关心与政治有关、有时也没有关系,因为台湾提供的资源是很丰富的,可是它被政治卷进去的时候也让人感到非常难受。那时候我经常说一句话“台忧亦忧、台喜亦喜”,这句话意味着大陆与台湾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文学台湾》出版后,《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介绍性的专辑,我曾提到孔子所说的,“鲁卫之政,兄弟也”,认为两岸之政,其实也是兄弟之政。因此,兄弟之间,或可因政见不和而相争,却不必因此而兵戎相见。如果你真把台湾研究当作一个事业的话,它还有个“疗救”、“疗伤”的功能。我常跟室里的同仁讲,要以“悲悯”的心情去介入。在理解这样一段民族分断的历史带来的伤害、悲伤与愤怒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赎救的道路,以文学的研究为民族的悲剧史做救赎。要把因民族分裂而牺牲受难的人看作为两岸的和平统一付出的代价,这样我们做这个工作才会更有意义。
研究室既然成立,那就要做得更专业,在学科的方方面面打好基础。比如说史料,要真正面对最原始、最可靠的资料,然后同情地理解历史和现实,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此外,我们要讲方法,要有良好的理论训练。理论会赋予你不一样的眼光,理论就像一束光,可以照亮那些黑暗中被遮蔽的史料。文学研究要三足鼎立,史料是一足、理论训练是一足、还有一足是文本解读能力。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作家留下来的文本进行细读。这是我们和历史学者、哲学学者不一样的地方。要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作品的味道风格、它夹在皱褶里面的那种血液,非常细微的东西往往就是作品中非常丰富的部分。作品的品鉴,涉及到对作品的好坏高下进行分辨和评估,这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能力。
进行学科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年轻人的培养。我对目前本学科的发展现状并不满意,有时甚至很焦虑。因此,看到年轻人进来参与这一研究工作总是很高兴,这个学科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过渡阶段”。我们从前辈那里吸收了营养,我们也要有所推进;有些我们做到了,有些要让下一辈或者更年轻的学者来弥补。
另外我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半外交性质的,这个学科一定会面临与自己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甚至学术训练都不一样的学术群体或者知识共同体,要与台湾、香港、海外学者进行对话。我提的要求是一定要有专业训练、一定要有对话能力、一定要有团队感。既然成立研究室,就必须把它做好;要做好,就必须注重年轻人培养。
你这个问题提的蛮好的,它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去做,然后我们怎么去做,怎样才能够持续地去做,要有一个很大的视野才可能把事情做好。
陈美霞:以前听说您对不同意见者比较宽容,今天听您说疗救、疗伤,我感觉好像比较理解了。
黎湘萍:要有那么一个心情——“悲悯”,这样各种各样对你的误解都没关系。处境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背后的因素,然后你才可能找到一个对话的方式,彼此疗救、彼此救赎的方式,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只从政治立场给人贴标签,因为在历史运动中的人是很复杂的。
(二)如何面对世界的整体性
陈美霞:黎老师,您富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性与浪漫性,有些知识对于快速的论文生产并无多大助益,但您乐此不彼!比如,您坚持学习拉丁语与希腊语,这看似与台湾文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你学这些知识是纯粹的兴趣吗?还是有什么动力?
黎湘萍:谁说与台湾研究没有关系呢?其实是有关系的。世界本来是很整体的,但是我们把它碎片化了。我们身在某一个碎片的时候,我们就自得其乐,就忘记它与整体的关系。
表面上看你是在做台湾文学研究,但要做好,要面临多少问题?刚才我说的三足鼎立:史料、理论、文本细读都需掌握。可是史料从哪里来?台湾问题的缘起在哪里?香港问题的缘起在哪里?澳门问题的缘起在哪里?或者中国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缘起在哪里?这个多重要啊!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做的东西就是零零碎碎的。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和视野是不一样的。比如,闽台关系研究,“移民”是个大问题,但除了福建移民外,台湾更早时候还有荷兰移民。
说到台湾的历史,在这样背景下,如何处理?台湾史既是中国史很重要的一部分,台湾史又是世界史很重要的一部分。你要把台湾搞清楚,就要把台湾世界史的部分搞清楚,把台湾中国史的部分搞清楚。世界史的这部分就涉及到荷兰人,荷兰人的问题就涉及到西方地理大发现。没有地理大发现、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就不可能有荷兰向世界各地的扩张。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了解荷兰人为何侵略台湾。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荷兰什么时候进入澎湖、什么时候进入台湾,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影响,荷兰人跟当时在世界称霸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关系如何?荷兰人怎么跟汉人交往、怎么跟原住民交往,留下了什么文化遗产,比如说基督教及其对原住民的影响,这是世界史面向的。只看中国的东西,不看西方的东西可以吗?这也是我建议年轻人学习荷兰语的原因。翻译都是有选择的,只有亲自摸索第一手资料才更有发言权。
从中国史的角度看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这又涉及晚明的历史,郑成功父子与南明政权的关系。明亡后郑成功为继续抵抗清人政权寻找据点,为南明政权延续香火。如果了解外文,了解历史,其实它不是孤立的。我现在跟你说郑芝龙是天主教徒,你一定会很诧异,海盗怎么会是天主教徒?郑芝龙怎么还有个外国名字,你在外国文献里看不到郑芝龙,你看到的是NicolasYikuan(尼古拉一官),一官是他的小名。说到这里又和澳门有关系,他曾经跟他舅舅到过澳门,澳门为葡萄牙人所占据,他可能在那里受洗。你看,他跟日本有关系,又和澳门有关系。光是这个人物,他牵涉的面就很多。清人把他看作贰臣,因为他翻来覆去,我们把他看作海盗,都简单化了。又因为他娶了个日本女人,生了郑成功,怎么说都不好,按照中国的现在的民族主义思维,郑成功的妈妈怎么能是日本人呢?可是生活就是这样。我做日据时代史料,发现《台湾日日新报》很喜欢谈郑成功的故事,日本人也喜欢用这个做文章,因为郑成功的身上有日本人的一些血统,他用这个来笼络汉人。你说我做的这个工作(学习多门外语)难道是没有关系的吗?
为什么外语重要?比如澳门,传教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跳板。澳门的“圣保禄学院”是中国境内最早的现代化学校,移植了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学的教育体制。“圣保禄学院”传授了西方的知识体系,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传授语言是意大利文、拉丁文或者葡萄牙文,特别是拉丁文。你不了解拉丁文你怎么了解这段历史?怎么知道圣保禄学院发生的影响?包括利玛窦在内的很多传教士到澳门,再从广东肇庆进入江西再到北京。第一次中外文化交流是从他们带来的意大利文或者拉丁文文献开始的,特别是拉丁文。徐光启翻译几何原理,是利玛窦口述的,这是最早的几何原理的翻译,不是在战争的背景下,是在非常和平常态的交流里开始。
让你们读亚里士多德,其实我意在此。除了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进行改造和扬弃,发展出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个哲学史的问题;其实还涉及到他是如何进入中国的,明代传教士就开始介绍他。最早汉译的文献,把亚里士多德论著翻译成汉语文言文,是从拉丁文的文本翻译的。
我看到年轻人,就主张他们去学点拉丁文,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分享我的经验。我现在很懊悔,或者说很奇怪,为什么我像你们那么年轻的时候没人来提醒我怎么去学。只要你掌握了拉丁语,你就可以阅读拉丁语系的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意大利文的相关文献,从而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初始状态。虽然说基督教(景教)在唐代就进来、元代也有人介绍,但真正发生影响是在晚明。而晚明与郑成功、与台湾有没有关系?这背后有我的问题意识。
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也好,都回到了中国的近代。中国近代不像日本人说的放到宋。宋代翻译佛经,新儒家(宋代)经过佛经改造,再把原来传统揉和起来,发展出像周敦颐、“二程”那路的新理学、新儒学,但这个东西还是以“我”为主,它的近代性还是很单薄的。可是到晚明就出现新的东西,如徐光启,很早就研究数学、历法、水利、军事。他给皇帝上过奏折,推荐“红蕃”(葡萄牙人)制造大炮的方法,想以此抵抗清朝入侵。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了中国的农业知识很丰富,他还吸纳西方农业知识。
我这样延展开来,你就知道要了解近代我们所需要的基础,多学几门语言,可以更好地掌握到我说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史料。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不能因为政治的隔断、朝代的更替而把它切断。这是个重要的视野,当然这是个背景,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不可能都铺到。但如果没有这个视野,绝对是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个就是求知的乐趣,延展开来,碎片背后是有联系的。
(三)理论与历史现场
陈美霞:我发现您的理论关注与一般人不同,比如《台湾的忧郁》、《文学台湾》,理论融入具体作品的分析;并非就理论谈理论,而是结合具体的语境,您在运用理论的时候很注重理论产生的背景脉络。您曾说过您从唐弢先生处获益最大的是“历史感”,这对您学术研究的最大启发是什么?
黎湘萍:以前赵园老师为《台湾的忧郁》写书评的时候,她对我鼓励有加。她的一个感觉是我太喜欢理论,她说《台湾的忧郁》理论概念不多,但似乎有理论的底色。我原来是学习文艺学的,虽然我不是很好的理论学习者,但确实非常迷恋理论。我的藏书一大块是外国文学、一大块是中外理论,我让自己尽量系统地了解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从苏格拉底及他以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罗马时代、中世纪到近代,思想史哲学史发展的过程和脉络,在不同地方开出来的路径。比如说在德国,它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繁盛的时期,黑格尔、康德……我都用很多精力阅读。虽然没有专门写这方面的文章,实际上那是我八十年代阅读的重要动力。
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必须要回到历史的现场。文学是情感的虚构的,可以说是想象领域的历史。可是进去后,原来很多抽象的东西会具象化。我们在跟唐弢先生这样一个作家型学者学习的时候,会发现光有理论是很苍白的。
跟唐先生读博时,我主要是到他家听他谈话,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文学也是生活化的。文本化的文学世界或者文本化的历史,是由一篇篇作品组成的,或者变成期刊报纸上的资料,可是这些是谁写的?是人写的。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不同立场的人、一个个有不同利害关系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有很多非常微妙的关系,唐先生很少跟我们谈具体的文学,但是他会跟你谈文学背后的人的故事,这样,我们就明白文学史对他们来说是活的文学史,是活着的流动的文学史。
我们年轻人很容易只看到文本,可是对唐先生他们来说,不是这样的,他看到文本背后的很多问题。这些老的学者作家,他从某篇文章的某个句子里,他知道这个句子说的是谁。比如鲁迅和周扬的论争,在什么情景下发生?现代文学中“两个口号论争”是怎么回事的?表面上是一个理论的论争,或者是关于统一战线的不同的理解,实际上背后还有更复杂的东西,不身在其中的人不能了解得很透彻。唐先生还活着的时候,现代文学、五四文学以来的文学对他来说还是活着的,当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很后悔当时没多问唐先生些事情。不断有老人走了,以人的去世为标记,历史也会走向终结,留给我们的是文本、或者说是史料、作品。最后我们只能凭这个东西来走近历史,你说我们得需要多少小心。这就是唐弢先生给我的启示:“历史感”很重要。
而我们年轻人往往容易忽略历史感,虽有理论热情。有时候甚至有理论没有生活,还丧失了常识。比如说关于最近的三十年历史、文革历史,很容易通过文本把它美化,其实就是缺少常识。有时候从常识判断比从理论判断更重要,这不意味着理论没有价值。比如,康德理论的价值还是在那里,但必须回到它的语境里,这个理论才会更丰满。
陈美霞:黎老师,您的理论深度有点遮蔽了您的史料功夫。其实您也很重视第一手的史料,近期您主持《台湾文学史料》编纂可以说集中体现了您的史料重视程度,丛书何时出版,据悉是工具书性质的?
黎湘萍:《台湾的忧郁》、《文学台湾》只从文本上看好像没下史料的功夫,其实我是从一本书追到一本书,它的版本、最初出版的年月,我都列了个单子下来。这个工作是大家看不见的。
另外,博论选陈映真,除了他的气质、他叩问问题的方式、他在台湾文坛特有的位置吸引我,还有一点就是《陈映真作品集》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资料,我才敢选他;如果没有,我也不敢做这一研究。很多台湾作家作品当时都没结集出版,至少在中国大陆是比较难找齐相关资料的。
我们把“台湾文学史料”的编纂与研究作为训练青年学者的一个方式,就是让他们每个人都亲自去触摸、去整理、去分析、去编纂这个史料。“台湾文学史料”课题的申请与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的成立几乎同步,这是研究室成立后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从晚明台湾问题的出现开始,暂时是终结在1945年:明末到清初、清中期、日据时代,日据时代又分为日文与中文的。现在基本都已整理好,但还需进一步注释,这样就能比较完整地呈现这一段史料。还是那个想法,史料是基础。
(四)探究经典与民间智慧
陈美霞:您身边的朋友、同事都知道您很推崇《圣经》,曾有学界朋友认为这是受到您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陈映真先生的影响,那么您关注《圣经》的最初契机是什么?兴趣久久不衰的原因是?
黎湘萍:应该说我很早就关注《圣经》。我的兴趣是英文和外国文学,但因家庭背景无法报考。即使是在学中文,我也花了很多时间自学外语。学英语的人都知道两个经典是英语文学上最常被引用的,一个就是莎士比亚、一个就是《圣经》。为了了解这两个(经典),就不断地搜集它们。除了看翻译的,还尽可能去找原文,有朋友去英国,我就托他去买KingJames版“圣经”,这是较古的英文版本。
第二阶段是1983年左右到南宁进修。我原来所在的县城没有教堂,南宁有基督教堂,配合我的学习以及对外国文学的兴趣,我就到教堂去。以前我只是从文学的角度理解《圣经》,七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我对“诗箴”、“雅歌”、戏剧性的“约伯记”、精彩的短篇如“路得记”感兴趣,“创世纪”我是当作神话来看。可是,1983年到南宁的时候我就想,它(圣经)在生活当中会是什么形态?就是它被人家阅读或者被信徒所信仰的时候是什么形态,所以我就到礼拜堂去观摩,看是怎么回事?这样可以帮助我了解这本书跟现实的人的生命的对话关系,这对我这样的非教徒的人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与七十年代末当作外国文学的一部分来读是不一样的。到1983年我觉得是一个转折,就是希望了解《圣经》与现实的对话关系,它作为信徒的信仰基石怎样去发挥一个指导性的作用。
第三个阶段就是碰到陈映真,他的作品有我感觉到的独特的思想性和诗性,散发着基督教的忧郁气质,这个气质是别的作品没有的。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有了前面的经验,我就更能够较容易地进入陈映真的世界,而不是相反。
《圣经》是真正的经典,而不是我们学科意义上的经典。什么是真正的经典,就是影响了人类好几千年的这些书,《易经》、《圣经》都很重要。我觉得要读这些书中之书、书上之书,读“书王”。因为它是源头,由它延展出很多很多的书。与其去看那些“流”,不如去看那些“源”。孔子、儒家的思想很重要,可是儒家之前的思想形态是什么,你还得回到《易》,回到更早的时代。这就是我不断地让年轻人阅读经典的原因。
陈美霞:除了《圣经》外,您对《易经》也相当精通,甚至对很多生活常识,“名学(起名字)”、血型等各种偏门冷僻知识,你也很认真地去关注去钻研。
黎湘萍:这个是“杂学”。中国文化很复杂。我为什么要学《易经》?除了是经典、是“源头”外,最早的理由是想知道孔子是怎么读《易》的?有句话说孔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他的进德之阶。可是,据说“孔子五十而学易,韦编三绝”。正是在他学易的年头,他“知天命”。接近孔子也好、或者后来的宋儒像朱熹也好都需要回到《易》。朱熹学《易》前焚香、祷告,按大衍之数算个卦出来,这并非迷信、这是他们接近《易经》的一个方式。
占个卦,卦占出来就有个“象”,再分析这个“象”背后有什么关系?它预示了什么?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哲学与杂学,二者是混在一起的,渗透在中国文学的方方面面。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在谈到《周易》、《易经》的时候,它还专门有一章是说“卦辞”,算卦的方法。一个很正经的哲学史都必须回到这个,因为这包含着中国古人的数理知识。从“数”变成“象”,再由“象”变成“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易”的哲学与智慧是比孔子要古老得多。除了了解西方,我也让自己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根底。避免谈西方天花乱坠,却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是怎么走过来的。影响我们几千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些都还在民间生存着。不了解这些,那我作为一个读书人,像话吗?我首先是个中国的读书人。我不了解中国的文化根源,当然不行。
陈美霞:老师,我听说您会算卦?那么您会根据自己算出来的卦象的预示来行事还是仅仅是为了好玩?
黎湘萍:不会,有时候只是为了了解。不一定是用它来预示,这并非跟现实有什么对应的关系,而是观察中国人怎么看待“易”。比如一个“卦”有六个“爻”的变化,这变化是永远的。现在留下来的64卦,它的卦辞、爻辞是固定的,因为它已经文本化了。如果你只是在固定的状态里去了解它,你对《周易》的了解是死的。卦原是活的,处于变化当中,它比黑格尔的辩证法还要辩证、复杂。
中国哲学很重要的就是“易”,“易”有三义,一个是“简易”;一个是“变易”、所以传教士把《易》翻译成“TheBookofChange”,就是讨论变化的书;一个是“不易”,即不改变。“易经”是用一个最简易的办法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世界是变化的”。这三个“易”就在里面了,可是光这样是很抽象的,你用一个“爻”、“卦”算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说的是有根据的,因为卦算出来之后爻和爻之间的变化,六个爻里面彼此之间的关联,每个都有象,象外有象、象内有象,意在言外、言在意中、言在象中等等。
不了解这个,就不了解我们的哲学、美学、艺术,也不了解我们的民俗社会。现在我回到民间,我也能够用你说的“名学”(起名字的学问)跟老百姓交流,因为那里面暗含一些“数”,有时候会对他们起到一些好的作用、治疗的作用。但是这个治疗不能说是空的,我给孩子起的名字,要经得起考验,我要对这个孩子负责。起名不是简单地要一个意义,里面蕴含中国哲学当中的“数”,内在的数理有些暗示的作用,你不一定要相信。但是既然是在这个文化语境里,人家又找到你,那你就按它的哲学给孩子起个好名字,祝福他。
陈美霞:在现有的学科体制里,台湾文学基本是属于区域文学,但晚明以来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势力的介入,使得台湾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的先锋区域之一,所以应把台湾问题置于东亚史甚至中西文明碰撞的历史加以考察。《台湾的忧郁》、《文学台湾》的阅读经验与本次访谈,都让我感觉到您不拘囿于学科界限,台湾文学似乎是您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您结合自身学术历程谈论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学科建设、理论与史料问题,台湾文学与外语学习背后的整体性视野等等都很有意思,相信对有志于台湾文学研究的年轻人会很有启迪。黎老师,谢谢您接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