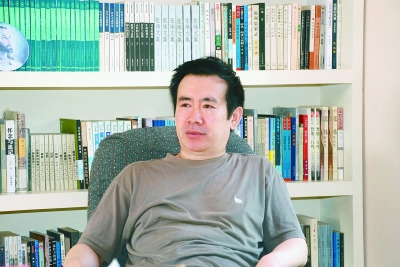
记者:您曾对作品进行过多次修改,有的是增补,有的是删改。原因是什么?
张炜:《你在高原》中的几部,以前出过单行本,后来发现全书写作时间漫长而且篇幅巨大(长达22年、39卷、450万字),必须停止单独出版其中的某一部。提前出版的部分,会与后面完成的全书在情节等方面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巨量的工作,需要全部完成之后,进行从情节到细节、从意境到结构的仔细调整、修订。所以这样的改动是很好理解的。原来出版的几部也就废掉了,它们在全书一起出版时,都经过了重写或重大的修订。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既有《心仪:域外作家小记》,又有《楚辞笔记》这样解读传统文本的作品,更有疏理齐鲁文化特质的《芳心似火》,可不可以梳理一下您的精神资源?哪些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张炜: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雅文学、思想类著作对我影响较大。具体说诸子散文和诗词对我影响最大,其中的儒家文化和齐文化对我的影响较大。
记者:我知道您特别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和鲁迅。有评论家曾说:“每一个中国作家的背后都有一个西方老头的身影。”在您看来,外国文学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张炜:我背后有许许多多作家的身影,而不是“一个西方老头”可以概括的。他们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老人和青年、古代的人和当代的人,是许多作家对我的综合帮助和影响。当然我也有特别喜欢的作家,这个对谁都不例外。如中国的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东坡、鲁迅,外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索尔·贝娄、福克纳等一长串名单,简直历数不尽。外国作家不如中国作家对我的影响大,所有的影响都是综合的,不会是某一个方面。
记者:您的“散文随笔年编”“中短篇小说年编”和“长篇小说年编”已经推出,通过梳理您的文学历程,您认为文学是什么?其价值在哪里?您怎样看待书的厚度?
张炜: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文明积累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综合呈现思与诗的文字。它是探究和接近真理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诗性写作的重心就尤其不是消遣。不能对真理保持深刻的热爱和探求心,不能严格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作品数量再多都是毫无意义的。
记者:之前您跟王光东有过一次对话长谈,跟这次《行者的迷宫》有何区别?
张炜:那是十几年前的一次电邮对谈,不是采访。这部《行者的迷宫》是采访录,由11次采访实录组成。十几年前的笔谈主要是文学问题,这一次采访包含的内容比较复杂,文学只占一部分。
记者:您的新作《疏离的神情》是在万松浦书院春季讲坛的授课记录,涉及艺术批评、文本分析、阅读欣赏等。您怎样看待作家老师和一般大学老师的区别?成立书院的初衷是什么?
张炜:这部授课录基本上是实录,尽可能地保留了现场感。我不太可能按照教科书来授课,因为那不是我的专长。来书院听课的人大多是大学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他们一直在大学里听课或工作,再听大学的那些课程就不需要到书院了。这里常常有对话和讨论,综合的东西比较多,话题也很宽泛。书院的设立,本来就是为了个性教育,为了继承古代的书院教育传统。
记者:真正的文学需要怎样的批评?
张炜:需要尖锐的批评、深刻的批评、感动的批评。
记者:全民阅读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您希望民众读怎样的书?您心中的经典是怎样的标准?
张炜:最好不读或少读流行读物,因为那是没有多少益处的。多读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中外经典。一个优秀的民族绝不能关在经典的大门之外。
记者:您是从写诗歌走上文学道路的,也出过《皈依之路》、《家住万松浦》、《夜宿湾园》等诗集,但您的散文和小说往往更能引起读者的反响,您怎样看待这种错位?
张炜:对于真正热爱自己文字的人,对于一个深入心灵探究的写作者来说,他可能并不太在乎所谓的“反响”。我一开始就写诗,一直没有间断。今后我可能还是将诗的写作作为最重要的创作内容。诗是隐秘和放肆,还是沉迷与玄思,是其他文体难以取代的。








